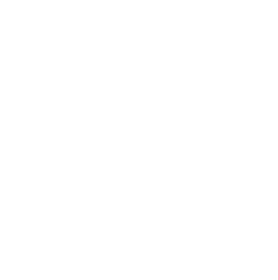赵青尧恍惚了下,对面的女人穿了件杏色羽绒服外套,质感绵软厚实,或许因为流产不久,脸色是捂不暖的白。
她的眸子黑白分明,和从前一样,宛如两池清水。
在去年某个夏日,赵青尧记起,两人也是这样相对而坐,景致截然不同。
她推开咖啡馆的玻璃门,以相亲对象的身份坐在他对面,羞涩,拘谨,还没说话,脸已经红得烧起来。
那时候的夏夏不是这样,不是眼前这个苍白、残弱、散发着病气的女人。
交往小半年之后,他向她求婚,赵青尧使劲回想让他那一瞬间冲动的理由,他最开始是怎样萌发了念头,想和她步入婚姻的。
记忆在脑海里蛮横地冲撞,像是海浪在身边狂啸,载着他努力在去捞取某个遗忘的记忆点,心脏抽疼起来。
“你每天都很开心?”
晚风微凉,拂得老街上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他低眼看着身侧的女孩,她正端着盒子,拿勺子郑重挖起一块奶油蛋糕。
“……也不是。”
她咬住勺子,嘴角沾着奶油,声音低不可闻:
“你和我在一起,难道不开心吗?”
“我不优秀,也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对象。”
迫于父母压力和她相处一段时间,赵青尧淡声道:
“电话里说可能不太正式,我的意思,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
“你很优秀的。”
奶油盒子啪地掉在地上,她紧紧捏着勺子,语气却格外柔软:
“你很优秀的,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好。就算被别人否定得一无是处…….”
她顿了顿,眼睛发红,显然是被他拒绝交往的情绪上来了,但还是很温柔道:
“就算被别人否定,也不要忘了爱自己。”
这番话让他第一次,仔细看了她一会儿,轻声道:
“没有权与势,我只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普通人,你高看我了。”
即使他年少时在学校如何天子骄子,光环耀眼,出了社会没有权势托身,瞬间被打回原形,碌碌无为,疲于为生活卖命。
“权势?啊,这当然是很好的东西啦。”
她挠了挠头发,显然这个话题离她太过遥远了,只道: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的,做……朋友也挺好的。”
街灯次第亮起,散出融融的光晕,映得她眼睛微红,眼角边有透明的水光溢出。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她竭力平静,可是手腕已经颤抖了,努力缓和呼吸:
“权势?这些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也是普通人。你是在担心普通人的生活会经历更多风暴?婚姻更不稳定?没关系的。”
她浅浅笑了一下,因为眼角有泪,显得那笑容有些伤心: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如果我们有机会步入婚姻,只要你不做让我很伤心很伤心的事。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天空,我愿意和你一起承受任何风暴,不抛弃,不背叛,直到死亡的尽头。”
“不好意思,我可能话有点多。”
她声音闷闷地,弯腰去捡地上的奶油盒子:
“其实…….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
她捡了盒子之后没有抬起头,转身走向来处。
他看着她的背影怔在原地,回过神时手中握紧了一截纤细手腕,肌肤相碰,她的体温化作一股暖流,流进了他的手心。
“前面有蛋糕店。”他说,“我们再去买一份。”
……..
而现在…….
他怔怔看着对面的女人,她情绪低落,几乎不与他对视,即使看过来,眼里也泯灭了喜悦的微光。
“那天的事,你怎么不说实话?”沉寂的气氛中,时夏道:“毕竟这次是我犯了错。”
这种事情,瞒着长辈总比坦白好,不是吗?”赵青尧抬起双手抹了把脸,有些事情,他不想现在问。
气氛已经够糟糕了。
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时夏却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无限漫长,她望向墙上的电子钟,迟疑该不该现在提出来。
注意到她总是看抬头时间,赵青尧目光黯了黯:“夏夏?”
“嗯。”时夏心不在焉。
“如果,我说如果我在里面呆几年时间。”
赵青尧一边开口,一边观察她的反应,可是在那张小脸上看不出特别情绪,他缓缓道:
“我知道这样很自私,但是…….你愿不愿意等我?”
为了应对审判,他委托了好友华严做刑辩律师。
真实情况或许严峻不少,华严通过业内的人脉渠道了解到,陈屿身份特殊,似乎与公权力关系不简单。
华严向他透露,即使他的案件性质更倾向于故意伤害罪,但检察机关准备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犯罪性质,量刑起点天差地别。
“我…….”时夏喉间微哽,顺从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不起,我想离婚。”
她补充道:“我可以净身出户。”
刑事犯罪,赵青尧优渥的工作注定黄了,出狱之后也留了案底,后面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时夏不惦记着公平分割财产了,她愿意净身出户,毕竟她有错,毕竟家里的大部分财产都是他赚得。
“我不同意。”
眼角猛地抽动,赵青尧努力心平气和:
“我不会签字,你可以选择诉讼离婚,但是至少满足分居两年以上的条件。所以这两年里,我们还是夫妻。”
协商无果,监警押送赵青尧回监房,分别前他的那一眼温和又冷漠,一如他的口吻: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他的嗓音低沉,坚定:“我们还会有孩子的,我们的孩子,我会让他回来。”
温和中别有一股无形阴冷。
坐在长凳上的时夏如坠冰窖,后背尽是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