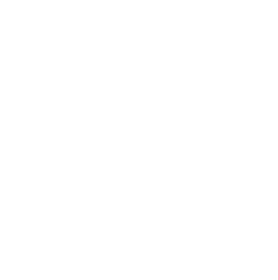繁茂的灌木丛和巍峨古树纵横交错,把这地方切分成很多狭长小径,哪怕在白昼时,此地也密布着憧憧阴影,人们的视线会被遮挡,行动的声音也会分散。塞萨尔不了解巫师,不知道环境对谁更有利,但总比在开阔地冲锋来得好。
他抓起长剑,就着清晨的雾往灌木丛中扑去。藏匿身体的同时,他感到细碎的树枝在自己脚下粉碎,发出啪嚓声。
刚往前跑了几步,他就听到摇晃的枝杈间传来了幽暗的低语,那是人类不该发出的声音,仿佛蛇群在林中吐信。晦暗的光线在晨雾下蔓延,形如阳光射入湖泊之底,显得诡异莫名。
尖利的嘶鸣声忽然间炸开,空气如受摩擦,吱呀作响,塞萨尔听到树木被穿透,看到木头碎片炸开,枯萎泛灰的枝叶四处飘飞,形成扭曲的漩涡。但他发现巫术的落点并非他所在之处,于是他轻呼了口气,继续快步前进。
税收官的仆从们大多惊慌失措,有些往外奔逃,有些在古树后缩成一团,但也有人结阵护住了年轻的巫师,把她挡在身后。
塞萨尔刚在灌木丛中现出踪影,一支弩箭就带着强烈的破风声迎面而来。不过,在失血过多的他眼中,这东西速度不快,像是只老鼠缓缓游过粘稠的黄油,极其艰难地剖开了四处弥漫的雾气。
他抬起手,抓住这支箭矢,几乎感觉到绷紧的弓弦将其射出那一刻发出的微颤。
箭头是钢制的,边缘极其尖锐,不可避免地切开了他的手掌心。剧烈的痛楚让塞萨尔打了个激灵,刚安稳下来的心思也消散了。无论力量怎样增加,感知如何敏锐,他依旧还是个脆弱如纸的人类。
把自己彻底转化的想法骤然膨胀开,像暴风雨一样在他心中酝酿起来。
不,不对,没这个必要。
塞萨尔强迫自己按捺心思。他不是饥饿的野兽,不能看到肉摆在前面就冲过去撕咬。
他稳稳挡开更多强劲的箭矢,手腕逐渐发麻,难以握紧长剑,却很快就在失血中再度激发出难以理解的力量。他抛出左手中那支箭矢,感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充满了自己的手臂。再一看,这一掷的力道竟插进了弩手的脸,使其脸颊在冲击中向颅内凹陷,血和骨片都从此人破碎的后脑勺里喷溅了出来。
沉默。塞萨尔感到有几个人注视自己的目光中带上了惊骇,但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什么。
那些人认识他,他想到,或者说,认识他现在表现出的诡异姿态。
这也许并不奇怪,祭祀异神阿纳力克的人不只是伯爵一个,完成了祭祀仪式的人也不只是他塞萨尔一个。也就是说,一定有像他这样的人曾经在世上散布过恐怖,然后被消灭。后世文献会把这些人的细节特征写得详尽无比,并力求追踪、查证和消灭一切拥有类似特征的可疑人士。
如果他猜测不假,那么,哪怕他逃出伯爵的城堡,他也难以在诺依恩的领地外求得安生。
不过还好,只要还没走到绝路,一切也都没差。他在上辈子就过惯了朝不保夕的生活,无非是换个地方重来一遍而已。
眼见无貌者正在另一侧和看不清面目的巫师纠缠,塞萨尔快步上前,劈开一个拦路者,将其半个脑袋都削得抛上了半空
2
。
剑刃划过之后,此人只余一个空洞洞的口腔含着半拉血淋淋的舌根胡乱弹跳,像极了盛在红酒杯里的水蛭。鲜血喷溅在塞萨尔身上,迅速凝结成暗色斑点,然后色泽变浅,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看到了他身体的异状,满脸惊骇,转身就跑,但他实在无法阻拦,既没心思,也没能力。他现在要做的是尽快解决一切麻烦,然后找个医馆,在他失血致死之前保住命。他继续快步上前。就在他要对华服的青年贵族动手的一刻,有人仿佛从虚空中浮现一样,忽然站在了他面前。
塞萨尔没仔细观察对方,下意识就要一剑劈出。这时,无貌者忽然惊叫一声,发出了不止是白眼的声音,——像是许多男女老少一齐发出惊叫。他反应过来这是警告,立刻往后退了两步,打量着眼前来历不明的家伙。
此人是从古树背后绕出的,魁梧的身形让在场诸人都相形见绌,只有塞萨尔除外。他的皮肤粗糙泛黄,有着宽阔的肩膀和脊背,腰肢相对苗条,但也只是对他来说算苗条。他那头蓬乱的黑色长发几乎冻出了冰凌,落到腰间,末端绑成一束,像结成锁链的野兽尖牙一样在风中飘舞。
对方穿着平常无奇的棕色皮革外套,破旧简陋,落满污渍,和那些干粗活的乡野猎户差不多。然而透过此人裸露的手臂,塞萨尔感觉他绷紧的肌肉在翻涌的晨雾中蠕动,许多肌肉的连结方式绝对不是正常人类该有。
来历不明的人往前踏了一步,和塞萨尔保持一步之距。那双乌黑的眼睛睁得很大,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人把怒视着塞萨尔的青年贵族挡在身后,仔细查看了一阵塞萨尔两侧散落的尸体,然后对他咧嘴一笑。
“那是草原人的剑舞者!”
假白眼的喊声传了过来,但塞萨尔一言不发,只是警惕地观察对方。那边的巫师也陷入沉寂,似乎觉得事态并不对劲。
塞萨尔自然不明白剑舞者有何含义,不过,草原人出现在一个为了抵御草原人而设的要塞中心,还是为了保护一个身为世代仇敌的贵族青年,这事的含义就很微妙了。
结合巫师的反应,他已经想象出了一套里应外合拿下诺依恩要塞的叛徒计码。阴谋的发起者就是跟着税务官过来的青年贵族,也即塞恩伯爵的侄子。
如此想来,诺依恩这地方实在离奇,要塞的城主是个在城堡地下塞满了孽怪的邪教头子,和他有家族分歧的兄弟又联合了王国外敌,想要引狼入室。
这边疆要塞多半是没救了,要么亡于城主的邪教祭祀,要么亡于草原人里应外合的围城战。至于塞萨尔,他可没有能力或义务救这地方于水火之中。
“na’v kouk!e’jiu!”
剑舞者说了句听不懂的语言,声音强而有力,像是种挑衅,也像是在邀约决斗。然后他就张开手无寸铁的双臂朝塞萨尔走来,微笑的表情仿佛是要拥抱朋友。他步步逼近,每一步都比塞萨尔后退的步伐迈得更大。
塞萨尔完全听不懂这人在说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失血更严重了。他必须速战速决,不然性命难保。
他一剑劈去,划出宽阔的弧形辐光,依旧毫无技巧,全靠无法理喻的蛮力。然而草原人抬起右手,直接用拇指和食指挟住了剑刃。跟着此人把腕部一扭,竟把长剑拿到了他自己手里。
塞萨尔无法理解对方是怎么做到的,——他手臂肌肉扭动的方式会把一个正常人类的韧带直接拉断。
剑舞者转了下手中长剑,描绘出一个完美的圆弧,带着旋转的惯性将其反手一掷,就朝塞萨尔的来路抛了过去。两个仆人正连滚带爬地逃出花园,想要给税务官或塞恩伯爵报信,却被长剑正中后背。
看到草原人也想灭口,塞萨尔心里的猜测更笃定了。
这一掷使得剑刃如陀螺般在其中一人背后转起了圈,割出条从后脑直达下腰的大豁口,然后带着破碎的尸体穿到了前一个人身上,好似把两块肉穿上烤肉的扦子。意图跑去报信的俩人狠狠撞在一起,四肢交缠着跌入灌木丛中,砸出哗啦巨响。
剑舞者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接着就朝塞萨尔撞了上来。他只来得及伸出胳膊,抓住对方的手腕,就跟这抛掉了武器的家伙缠斗在一起,好似像两个摔跤手。看到他很配合,对方嘴咧得更大了,模样极其兴奋。
塞萨尔能看出来,草原人想拿文献记载里的邪恶事物试手,像这样在死斗中展现自己勇猛的气势,在他们眼里可能是非常光荣的。
好在,他虽然没练过剑,——有枪械可使,他为什么要练剑?但他玩过搏击。哪怕没什么造诣,至少也不会像使剑一样全靠直觉乱抡。
然而塞萨尔也不认为自己能在近身搏斗中胜过对方。群'6#999四;:9三!6壹!999
此时此刻,除了他和无貌者以
3
外,在场诸人分为三种:
一种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无知者,也即那些税务官的仆人。他们要么就是在逃跑时送了命,要么就是死在塞萨尔手里,只有几个还在树背后抱头颤抖的人性命尚存,但是,他们影响不了任何事。
还有一种,是对里应外合有所预谋的阴谋参与者,伯爵的侄子和保护他的草原人剑舞者正在其中之列。那几个持剑卫士并不明确,不过,已死之人也无所谓了。
最后一种,就是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但有能力做出选择、影响现状的本地人,那个忽然停下施术的年轻巫师正在其中。她陷入了迟疑,从和无貌者纠缠变成沉默这对峙,是因为她还在思考和判断,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塞萨尔知道,他在诺依恩的命运正在按照两场荒唐的赌局进行。是被塞恩伯爵逮住,尸体绑上石台献给阿纳力克,还是许多天后在草原人破城的时候死于乱军中,两种下场能有多大区别?
逃出去很难,他要做的,也许不止是应付眼下的局面,还有更后面的局面。为此,动摇那个还在思考和判断的巫师学徒非常必要,说不定,之后逃出城的事情就得指望她了。
他是只瞥见过对方的大致轮廓,其它一概无知,但无貌者不同,无貌者已经和她纠缠了很久,还占了白眼这么一个熟悉的身份。要知道对她来说,白眼的话可是比在场其他人都有分量——她是女巫的孩子,白眼是女巫的仆人。
除了女巫柯瑞妮本人,没人比白眼认识她认识得更久。
“跟她叙旧,问她想不想保命!”塞萨尔抬高声音喊道,“跟她说我看到了要塞陷落的预兆,说草原人已经要围城了,要想自救,就先合作逃生!”
说自己看到了要塞陷落的预兆,这当然是他在胡说八道,假冒先知,说草原人已经在围城了,这自然也是他在胡说八道,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当然,他胡说归胡说,伯爵的城堡里已经出现了里应外合的草原人,这座要塞是个什么情况就很值得怀疑了。
单纯的怀疑分量不够,至少是不足以让人改变想法,所以,塞萨尔得把担忧变成确凿无疑的相信,让对方以为他是真的知道些什么。
就像他让无貌者觉得,塞恩伯爵是真的会把她扔在城堡地下不管一样。
若不是语言不通,他现在已经在言语动摇那位年轻的巫师学徒了,——无非就是多用点引导的话术,算不得难事。他能改变无貌者的想法,是因为他本来就很擅长跟自己的人类同胞用类似的话术。
至于现在,塞萨尔只能希望假白眼的口才比伯爵的侄子更好,能在争取信任的比试里取得上风。
见对手竟然不集中精神决斗,剑舞者仿佛受了侮辱般怒视过来,看得他心里一颤。似乎是因为他侮辱了神圣的仪式,草原人大吼一声,摆出推车的姿势往前冲,势要把他砸在墙上。塞萨尔也效仿对方用了一模一样的姿势。
虽然他俩肌肉结构差得很远,但大量失血给他提供的力量竟然让他止住了对方冲刺的势头。塞萨尔浑身用力,青筋暴起,伤口又开始喷血。
剑舞者喉头蠕动,发出一阵嘶吼,双臂一沉,压得塞萨尔腿脚不稳,跟着那双强壮手臂直接往上扬起。这一下摸准了他稀烂的下盘,当场把他像铁饼一般甩了出去,几乎要抛飞到半空中。
塞萨尔狼狈地滚过一堆灌木丛,好不容易才稳住平衡。他在地上猛得一蹬,想要站起身来。然而他刚伸出去脚,他就见草原人抬脚下踢,势头极重。
他勉强用手臂挡开一脚,感觉骨头被踹碎了,发出凄惨的咔嚓声。跟着又是一脚。
剑舞者是打算下狠手杀他了,看来在草原人的比试里,率先倒地者就算是失败。既然他已经失败了,也就没什么遵守比试规则的必要了。或者,在草原人的传统里,这种死亡也只是一起不幸的事故,在他们的厮打里非常常见。
拜托——
他是不是不该让无貌者从叙旧起手慢慢谈判的?
一道令人目眩的强光忽然炸开,塞萨尔差点以为自己挨了一发闪光弹。眨眼间,他们所在的大片区域都被夏日正午般的白光笼罩。他听到剑舞者发出怒吼,似乎是在斥责阴险的巫师,他知道这是为了迷住剑舞者的视线,因为最刺眼的光乃是从他背后射出,径直扑入剑舞者的眼睛。
能借机杀死这家伙吗?
“跑!”假白眼高声喊道。
看来这想法是个错误。塞萨尔立刻往一侧滚开,朝反方向奔跑,跟着记忆中的方位往花园缺口处逃去。
这一刹那,他听到草原人的脚舞者一脚猛踏在地,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大片泥土和灰烬向外掀起,如一场泥石流砸在他背上,震得他身子都晃了一晃。他几乎要被掀飞,但还是脚步踉跄地往前扑,一边维持平衡,一边手足并用爬起来奔
4
逃。腿骨的伤势似乎不怎么影响他的动作,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还有,这家伙当真是使剑的吗?
好在他还没流血致死,还能无视自己身体的虚弱继续行动。
一片混乱中,一只手忽然扶起了他,“快跑!”塞萨尔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跑,大步跃过地上的死尸。他在土坡上绊了一跤,还是坚持用最快的速度往下滑,无貌者用手臂在他身前阻挡鞭子一样抽打过来的树枝。剑舞者的吼声更强烈了,似乎就在背后,塞萨尔则跑得更快了,身后还跟着个和人隔空喊话的女巫。
虽然听不懂她在喊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也许就是在对骂。那个伯爵的侄子正在大声诅咒她,语气里颇有种到手的鸽子飞走的狂躁感。这算是他拐带成功了?他也不清楚。
一片飞扬的尘土中,塞萨尔看不清太多东西,只觉刺骨白霜和浓郁的血腥味塞满了他的肺。他还是竭尽全力在跑。只要能逃到城堡外的街上,谅这剑舞者也不敢公然肆虐人群,破坏他们草原人的计划。
那么诺依恩真会被蛮族大军围城吗?倘若要塞城堡地下的孽物倾巢而出,这场大战又会变得怎样?
拜托,那怎么也得等他自救成功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