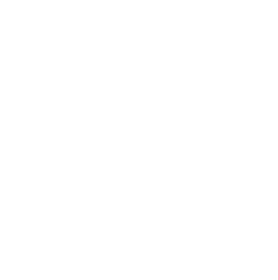畸形的孽怪往军阵狂奔,身下短小的腿脚疯狂挪动,快得像是在抽搐。塞萨尔实在说不清它到底是条蛆,还是条尺蠖。
它在火枪齐射下污血飞溅,身上挤压堆积的人尸纷纷支离破碎,所经之途散落了越来越多的残破肉块。尽管如此,它冲锋的势头仍然不减,倘若它撞向长枪阵,必定会碾死大片士兵,并将更多人裹挟在腐液和骨刺中咀嚼撕碎。
好在炮兵已经就位,炮弹发出轰鸣,正中那孽怪肥硕的身躯,触及的一切都像玻璃一样粉碎。在火炮轰击下,它一截截身躯都被碾得稀烂,散作满地硝烟弥漫的碎块。但是,它仍然在动,它用许多条畸形的短腿扣紧地面,奋力收缩躯体,往前挣扎。它的中部身躯被头尾挤得往上拱起,在半空中摇摆、晃动。
蛆虫似乎就是这么往前弹跳的?
塞萨尔实在不敢想象,这条巨大的人蛆砸入军阵到处翻滚会是个什么情景。这时候阿尔蒂尼雅指示炮兵换上了榴弹,轰鸣声更加剧烈地传出,那孽怪顿时被拦腰炸断,笨重地裂成了两大截。
从长枪阵的空隙里扔出了十多罐燃烧的火油,泼溅在人蛆全身,地上的碎块在燃烧,渗入了火油的尸堆也在燃烧。挤压到扭曲变形的一张张人脸长大了嘴,发出凄厉的叫声,发了疯一样伸展着腐败的手臂,想要触碰前方的生灵,但是,它们已然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炬,形成十多米高的烈焰照亮了整个农庄。
“军阵转向!”阿尔蒂尼雅大喊,“不要被诱饵迷惑,野兽人正在冲锋!”
这喊声提醒了塞萨尔,他看向城镇深坑的方向,只看到野兽人的一个小队,然后意识到它们相当于斥候。虽然阿尔蒂尼雅说失败品缺乏智慧,萨满都不想带着它们南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们似乎懂得战术。
可是,它们为什么会懂战术?从血脉中传承下的本能吗?还是说某种日渐累积的群体记忆?
都有可能,不过,后一种能解释更多东西。
倘若野兽人拥有日渐累加的群体记忆,那么卡萨尔帝国奴役它们的记忆也会日渐累加。无论一个野兽人是新生不久的,还是受迫转化而来的,千年之久的奴役都会刻骨铭心地烙印在群体记忆中,影响着它们的一举一动。那些拥有智慧的种群还好,那些智慧低下的种群也许并不能分清群体记忆和自身记忆的区别,对于这些转化失败的作品,恐怕它们根本没有自我,只是些持续着机械性行为的......
血肉人偶?
军队再度转向,组成应对敌军的战斗队列。塞萨尔骑马来到阿尔蒂尼雅身边,她看起来想要率领骑兵冲锋,但他按住她的肩部,对她摇了摇头。“你待在这儿指挥吧。”他说,“正好也一并指挥我。”
她稍稍睁大眼睛,“先生......”
“别用这么轻柔的语气对我说话。”塞萨尔望向城镇的方向,望向正在涌出深坑的混种野兽人,“你是最优秀的指挥官,我只是那个给你描绘蓝图、给你指引方向的人。你可以调度和控制整个战场,把它们当成你剑锋的延伸,而不是带着我们本就不多的骑兵冲锋陷阵。你已经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指挥所有人了,余下的事情,你只管交给那些听你指挥的人就好。”
“但您也不该冲锋陷阵,塞萨尔老师。”阿尔蒂尼雅说,语气还是奇异地柔和,“您无法被替代的实在太多了,失去任何一个我都无法想象。”
“这里没几个人适合带头冲锋面对那些疯狂的野兽,你一定是唯一的指挥官,而我至少不怎么怕死。”
她蹙起眉毛,“好吧,但在下次您不得不这么做之前,我一定会为我们找到能担当起职责的人。”
“这种人可不能凭空变出来。”
塞萨尔说,然后扣住面甲,骑着被迫伪装成马匹的妖精群往前行进。随着两位法师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他这身盔甲越来越沉重,已经没有正常的马匹能够承载了。不过,勉强维持人类躯体的受诅咒者,还有勉强伪装成马匹的集群孽怪,两者也许恰好很搭。
没有让它们化身成拟态红龙,也只是他考虑到现实的影响而已,实际上也不是做不到。这东西哪怕拟态成披甲的战马,也在咧着满口利齿喷吐血气,显然是对吃下鲜活的血肉感到饥渴难耐。
这些猩红色的小妖精满脑子鲜血和痛楚也就罢了,还非要杀死高等而非低等的生灵,塞萨尔再怎么强调老鼠、人类和野兽人都是肉,它们都死活不听。若不像个邪教徒一样举行血祭,他也只能依仗战争了。
塞萨尔披着全身重甲策马疾驰,率着一部分骑兵绕向右翼,左翼手持火枪的轻装骑兵由瓦雷多指挥。这位骑士已经历练了很多,对骑马射击和灵活机动也算是经验丰富了。在各个方面,他都对他言听计从,自从了解到他和皇女的关系后,瓦雷多更是把他当成了以后升迁的依仗。
当初他还觉得这些小贵族很难信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对青年贵族的行事方式了解太少。只要不是家族长子,只要不是能让人栖身的大贵族家系,有理想的青年贵族们自会互相抱团寻求其它出路。对于如今这个有军权、有领地、有帝国的皇室后裔的势力,很多人只要能站稳脚跟,是不会把他们本来的家族当回事的。
战斗号角鸣起,呼唤人们作战。长枪林立往前,火枪兵分列其中准备射击,炮兵开始按照瞭望员给出的方位调整炮口角度,准备以最稳妥的方式应对从坑洞中涌出的未知敌人。
天幕依旧阴暗,在靠近城镇巨坑的位置甚至透着血色,边缘处的土地呈现出猩红色,仿佛下过一场血雨。塞萨尔觉得血腥味越来越浓郁了,不仅让他心绪狂乱,盔甲下的血肉都怀着狂喜的欲望涌动起来,剧烈的喘息在他面甲下回荡,化作沉重的嘶嘶声,——他和人谈爱的时候喘息声都没有这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