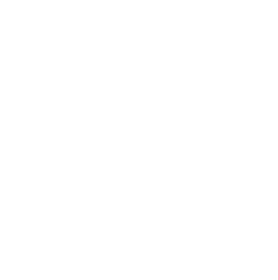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我没想过那个人会怎样,”狗子眨眨眼说,“不过,他也被波及了,肯定跑不出去。”
想到格兰利有可能已经淹死了,塞萨尔就心里一沉,然而他也没法子,这事只能听天由命。“沿河往前走吧。”他说,“想办法找到出去的路,最好也找到格兰利......活着的格兰利。我做了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消灭恶魔。我要得到神殿的支持,少了格兰利,事情可就没法办了。”
“也许这儿有出城的小路呢?祭司和他的卫士就是往这个方向逃的。如果能出去,主人就不需要算计这么多了。”
“事到如今,怎么可能一走了之?”
塞萨尔说完沿着来路摸了回去,从河岸潮湿的泥泞中拾起护身符,考虑到狗子的感受,他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把护身符裹得严严实实才揣进怀里。他这件衣服已经有些破了,不过比她切成了碎布条的衣服好点。他脱下棕色外衣,费力把它拧干,回身却看到这家伙上身一丝不挂,只在肌肤上贴着一束束金发,于是把衣服给她扔了过去。
狗子套上这件稍显宽大的外套。“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呢?”她盯着他,目光中带着好奇。
“菲尔丝还在上面。”他说。
“但她只是个诠释道途的工具吧,再找其他的不就行了吗?”狗子的红眼睛一眨不眨,脸上带着孩子一样平静的笑意,“有了密仪石,对付一个法师还不简单吗?只要找到他在乎的亲人让我杀害、取代,我就可以在他放松戒备的时机动手。等他失去了反抗能力,还不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正是因为她笑得像个孩子,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她这话才尤为恐怖。
塞萨尔看着无貌者用轻快的语气诉说残忍之事,不禁想到,菲尔丝和她相处了一个多月,如今在她看来,依旧是个给他诠释道途的工具。这态度从最初直到现在,没有发生分毫变化。
人在哪片土地待久了,难免会想扎下自己的根,和其他人相处久了,难免也会产生很多复杂的感情,有时甚至是情愫。塞萨尔像树木伸展枝叶一样和其他人的枝叶交错、重叠,既是为了和人们互相扶持,也是为了多了解一些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些伸展出的枝叶越繁茂,和他有交集的人就会越多,和他有交集的人越多,他也会变得更完好。
然而无貌者不同,她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她汲取的人格和记忆从来不会扰乱她,在完美模仿他人的同时,她丝毫不把他们的感情当回事。既然连感情完整的人格记忆都影响不了她,那么,人类个体之间产生感情的过程,又怎么可能影响到她呢?
乍看起来,狗子和菲尔丝共处了一个多月,彼此相安无事,还帮忙照顾过她虚弱的身体,可谓是关系和睦,感情充沛了。然而这只是塞萨尔的命令,从来没有改变过她本身的态度。她绝非人类这样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感情的东西,——她是把穿透环境的利刃,她切开人们相互联系的枝叶却不接在自己身上。她只是抓住这些枝叶,无动于衷地使用,好像是在使用工具箱里的工具。
没有人能在人类的社交行为中让她产生感情,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影响都难办到。这就是塞萨尔对她的看法,至少是目前的看法。
要真正影响她,似乎只能从无貌者本身成长的途径着手。如今看来,使她发生最大变化的契机,无疑是这头名叫白魇的恶魔。
难以揣摩的事情太多了。塞萨尔摇了摇头,如今想这事也没什么用,怎么着也得等到了依翠丝、接触了本源学会的法师再说。不是他钻牛角尖,非要和狗子的天性作对不可,是他越深入认识无貌者,就越觉得把她束缚在他身上的契约怪异莫名,令人心生怀疑。
“别在乎理由了,”他对她说,“你跟我过来就
5
好。”
......
河岸的道路往上倾斜,逐渐变得越来越陡。狗子在前方走得悄无声息,像是个静谧的幽灵,塞萨尔则脚步迟缓地踩在泥泞中,每一步都迈得很艰难。他一边缓缓挪动,一边用右手扶着岩壁,确保自己站在靠墙的边缘位置,只怕一失足坠入暗河。
这地方潮湿又打滑,黑得不见五指,很多时候,他只能看到一些朦胧的线条,勉强勾勒出坡道和河岸的轮廓。
越往上走,坡道就越陡峭狭窄,两侧岩壁也越发崎岖干燥了。摸索着攀登时,锐利的石块在黑暗中擦破了他的手,把本来痊愈的豁口又撕裂开。鲜血再次流出,让他又冷又不舒服,胃里也一阵恶心翻涌。
“这儿。”狗子抓住他这只右手,紧紧握住,“我就说你应该抓住我的手才行。抓紧一点,可以吗?我们就快到更上方了,——往上的坡道通往那处洞窟,往下的坡道通往城外。”
塞萨尔停下脚步,看着她。“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现在折返还来得及,主人。”
“我不想让我的挣扎白费。”
“虽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啦,不过,和折返回去逃出城相比,待在这儿会面对危险得多的状况,塞恩伯爵,女巫柯瑞妮,还有西边的萨苏莱人。如果你死了,我会吃掉你全部的血肉和灵魂,主人,你会为了自己灵魂的自由而挣扎吗?”
“已经走到这里了,也久没有折返的必要了。”塞萨尔说,“至于挣扎,我多少还是会挣扎一下,如果挣扎不过,你就把我吃了吧,”
狗子眨眨眼,没有跟他说更多,只是回过头,脚步轻快地继续往前走。忽然间,她跨过了一堆石头,他却没注意,一脚别在石头堆上摔了个跟头,左腿打着滑落到山崖外,悬在半空中。若不是她拽紧了他的手,恐怕他会从坡地一侧跌落暗河,再次被卷入激流。
塞萨尔拉着狗子站稳,扶着岩壁喘气,觉得心脏跳个不停,等缓过了劲,他才注意到别住自己脚的东西轮廓很怪异。他跪倒在地,后背靠墙,伸手在地上摸索了好一阵,才从碎石和尘埃中翻出一个人来。只见此人金属质地的护胸甲泛着微弱的光,竟然勉强照亮了这片黑暗狭窄的坡道。
是格兰利。
塞萨尔缓了口气,伸手想确认格兰利的死活,狗子却从神殿骑士身上翻出来一只金属酒瓶,给他递了过来。他本来也想婉拒,先看看这人情况再说,身体却一阵发冷颤抖。他当即接过酒瓶,拧开瓶塞,对着自己的嘴灌了下去。
直到咽下好几口后,他才把格兰利扶起来,靠在墙边。不得不说,这酒很烈,下了肚之后火烈燎人,迅速驱散了他体内的寒意。
塞萨尔揭开格兰利的面甲,发现此人呼吸还在,由于盔甲保护得很好,他的身上也没见伤势。神殿骑士昏迷在此,应该是受了跌落冲击,不过看他嘴边没有渗血,内脏应该也没什么大碍。
“让我吃了他怎么样?”狗子提议道,“我也可以当格兰利,而且会比他本人当的更好。”
她说的好像神殿骑士格兰利不是个人,而是一个身份,一个名叫格兰利的职位,如同诺依恩下城区的铁匠也是个职位一样。很明显,她是认真的,只要她想,她就可以杀害铁匠铺里本来的铁匠,把尸体吃掉,自个抄起打铁的锤子干这活,而且,她总是比那个本来的铁匠干得更好。
也许不同的人类个体,在狗子眼里就是不同的身份职位。只要杀害本来的雇工,拿到他们怎么在自己这个身份上扮自己的记忆说明,她就可以使用这个空缺出的身份。
未必也不是一种看待人和世界的方式?塞萨尔想到,虽然这方式确实很怪诞荒谬。
“不行,”塞萨尔否认了她的想法,“我说过不考虑再让你长期当另一个人了。”
“那我该怎么办?你都要我放弃力比欧这个身份了。”
“伯爵不会让矿区停工,你在矿道里耐心等到凌晨,等夜间下工的矿工要和凌晨上工的矿工交班了,你混进人潮就能出来。等出了矿区,你就去打听我的落脚处,拿着力比欧的信物找到神殿骑士。到时候,你说你是我的仆人就好。”
“好吧。”
想到力比欧,塞萨尔就觉得荒诞意味十足:“当时欢愉之间的人都认得你,以为你是力比欧拐来的小情人,现在事情换了个面目,那家伙的名声,多半也会从贪婪好色变成为信念牺牲......”
“那你觉得我扮他扮的怎么样,主人?”狗子问道。
塞萨尔想了想,说:“虽然说着很荒唐,不过,你假扮的力比欧是比本来的力比欧更好。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个值得尊敬的老战士,他的后辈也会认为他是个退役之后还不忘武技的好前辈,连神殿骑士也会对他报以敬意,书写几篇文章。那些流传在市井的贪婪好色的名
6
声,都会在这时候一转为虚假的污蔑中伤,给他的传奇故事再添一分色彩。”
狗子点点头,嘴唇带笑。虽然她不是有意重新诠释一个死去的人,不过听到他由衷的赞赏,她还是欢欣愉快。为了表达情感,她用双臂抱住他,给了他一个缠绵的湿吻。说实话他舌头隐隐刺痛,刚喝过烈酒,还有些发麻,但她的吻别具风味,烈酒温暖身体,她却能温暖他又累又冷的精神,搭配美酒会更好。他看到她两颊燃着红霞,眼睛也闪闪发光,知道这样抱着他亲吻就像他喝酒一样,让她感到神迷。
不过,想到自己是在神殿骑士头顶上和他们要征讨的恶魔亲热,他心里就有些发虚。
塞萨尔不懂治伤,对着格兰利了左思右想了一阵后,他直接架起了他,借着盔甲的微光给自己引路。等地底湍急的激流声几乎听不见时,他和狗子把人架出了狭窄的坡道,最终架到一处活板门前。他敲了敲头顶的活板门,不得其意,但也不多想,只管抄起钉头锤把木板门砸了个稀巴烂。
他俩把神殿骑士架到上方,然后挨个爬入,发现此地是个堆满了破麻袋和废矿的坑道,几件老旧的破矿工服堆在破损的推车上,正好适合穿来扮本地矿工。现在看起来,欢愉之间的祭司会往这儿逃,就是因为这条秘密通道。
倘若他们没带走神殿的财产,也许就能顺利逃出诺依恩,但是,既然他们带了,还落进了塞恩伯爵这个有心人眼中,最终落得这等下场也不能怪别人。
“就在这地方分开。”塞萨尔说,“再上去,可能就会遇见雇佣兵四处找人了。”
“那这通道呢?”
“留着,也许以后用得到。”
......
在希耶尔神殿人员落脚的旅馆住下时,塞萨尔发现,他们挣扎了这么久也没找出从下诺依恩逃出城外的法子,结果逃到最后,竟又从下诺依恩回到了上诺依恩。狗子离开以后,他扶着神殿骑士走了一晚上,走过狭窄的矿道和宽阔的台阶,一直到了矿口才发现了雇佣兵队伍,——他们其实已经在回去复命的路上,但伯爵派来的士兵堵住了他们。
这帮士兵不仅堵住雇佣兵队伍的去路,还看到了写在逮捕令上的塞萨尔本人。若不是神殿骑士强忍着不适喝退了他们,只怕塞萨尔要被强行带进监牢,第二天就生死难测了。
这帮见鬼的雇佣兵连埋在塌方中的格兰利都不想救,又怎么可能和城主对抗,保证他的安危?
当然说到底,格兰利也不是给他们付钱的那个,拿了力比欧捐款的大祭司才是。
塞萨尔架着神殿骑士一路走,走过宽阔的大街和内城的城门,在众人注视下走进大祭司落脚的庭院旅馆。这是座典雅的别墅,和下诺依恩的建筑以及氛围差距明显。等把格兰利送到大祭司面前,塞萨尔就拉着菲尔丝要了个小房间进去,——有些事情,他本人不在场时由别人转述效果会更好。
“明天就到决定我们下场的时候了?还是说今天就会?”等他关上房门后,菲尔丝发声问道。
“你说得好像我们是等着上绞刑架的囚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