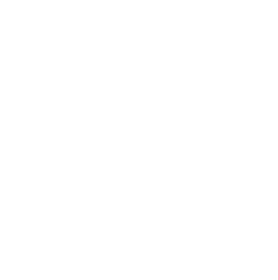当然,塞萨尔也看到了老米拉瓦,看到了塞弗拉一行人和她背上的他自己。老皇帝身着锈蚀的甲胄,正站在被封印的真龙正下方。他背上的吉拉洛已经快衰朽至死了,脑袋耷拉,身形枯槁,看起来送米拉瓦抵达封印之地才是他真正的使命。
老皇帝高举着手臂,吉拉洛握着他的腕部,以他最后的生命力为他呼唤穹顶的真龙,干瘦的手臂上闪烁着璀璨的符文。他的存在正在消散,起初还只是佝偻衰朽,接着已经无法觉察,只能看到一片阴影笼罩着米拉瓦,接引着穹顶的封印。
多枚闪烁着强光的金属矛撕裂了空气,如灼目的阳光从天而降,要贯穿米拉瓦的身躯。大多都在无形的壁障上擦向一边,深深刺入山岩刻下裂纹,扬起漫天尘埃,但还是有一枚径直洞穿了老皇帝的胸腔,把他牢牢钉在地上。
蛇行者始祖带着它的子嗣们漂浮在穹顶的黑暗中,环绕着真龙,誓要断绝人类攫取其遗产的可能。
血骨虽是传言中野蛮凶狠的食尸者领袖,却盘着腿悬浮在空中,姿态安宁,神情平稳,像神一样俯瞰着下方的米拉瓦。它十多枚血球似的眼珠中闪烁着洞察一切的光芒,——那些眼睛不像是食尸者疯狂的血眼,反而像是映出一切的银镜。
接受了思想瘟疫吗......
塞萨尔当然还记得那一刻的感受,他清楚记得,当时他怀有一种渴望,意图抹除他灵魂中一切属于塞萨尔的痕迹去书写思想瘟疫的真知。在那一刻,他的认知从刹那间的个体意识抬高到了无尽的永恒,在此等高度的视角下,没有任何人的价值高到可以永远存续,然而,思想瘟疫可以。
当然,思想瘟疫是外化的看法,他身处那一刻并触碰到思想瘟疫的污秽时,它就不再是思想瘟疫,而是永恒的真知。
所谓不可变更之永恒,不可损毁之真实,就是把他灵魂中会随着岁月流逝衰朽死去的事物全都擦除,改写为永恒的真知。他将从时刻衰朽的人化身为一本永不衰朽的书册,记载着永不衰朽的真知。这份真知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他那些时刻衰朽的人格意识蕴藏其中,就是在玷污,是在损毁。相应的,若把他自身献出去,则是在接受莫大的荣誉。
塞萨尔要献出自己的灵魂去书写它,就像法师的奴隶献出自己的人皮去书写邪咒。他的灵魂需要彻底清洗,把塞萨尔的痕迹清理得一丝不剩,奴隶的人皮也要彻底清洗,以免污垢损毁了法师想要书写的咒文。
这份危险的思考,恰恰会落在善于思考的人身上。其中,那些对永恒的真理怀有期许和想象的人特别容易受害。它对塞萨尔、对他身边这位蛇行者都有莫大的威胁,对塞弗拉这类人却毫无意义,对血骨这种荒蛮的野兽也毫无意义。
于是,事情就来到了另一个层面,——思想瘟疫会把肉体层面的残忍杀戮转移到思想层面中。智慧成为剑盾,思想成为利刃,拥有最高明智慧的人握着自己的利刃在思想的竞技场中一路厮杀,击溃所有敌人,其中胜利者将得到最高的荣誉,——用自己的灵魂来书写思想瘟疫的真知。
那位传闻中原始蛮荒的血骨酋长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它的大脑乃是思想瘟疫的竞技场,它的身躯乃是胜利者的座椅。它吃下的人都是竞技场中的斗士,握着自己思想的利刃彼此争斗,谁获胜了,谁就能坐在椅子上担当血骨,以它的名义在现实中传播思想瘟疫的诅咒。
血骨是代表思想瘟疫来到了此处,那么老皇帝呢?
塞萨尔低头看着米拉瓦,发现这家伙竟硬生生折断了金属长矛,把那半截如有实质的耀眼阳光从他躯体的血窟窿中拔出,几乎像是只恐怖的孽怪。
他看起来已经接受了一小部分真龙的遗产,躯体不断拔高,比塞萨尔在残忆中看到的米拉瓦还高了一倍。他健硕的上身已经撑开、撕裂了锈蚀的甲胄,仅有宽大曳地的长袍系在腰间,虬结的肌肉活像是苍劲的树干,腹部巨大的血窟窿里遍布着新生的血管,正像针线一样缝合他躯体的破损。
但老米拉瓦还是发出了狂怒的咆哮,——他躯体增长的速度忽然减缓了。
“血骨没有争夺真龙的遗产。”亚尔兰蒂从他背上飘了下去,“它在帮蛇行者的始祖,——那个注定会死的初诞者。”
塞萨尔发现他身侧的蛇行者正吐着蛇信,咝咝作响,顿时明白过来,这家伙也和他们想到了一样的事情。
“始祖......”它说,“我尊敬的母亲和当时所有诞生在墓中的始祖都交媾过,它不仅接纳了它们的种子,还吞噬了它们全部的血肉灵魂。完成这一切之后,它坚信自己孕育出的族群会超越一切。它只是条蛇,但我们拥有虚体、掌握着恐怖的力量、可以在虚空中肆意翱翔。现在看来,它仍然没有满足。”
考虑到初诞者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牺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繁衍的族群,那么,血骨让它接纳真龙的遗产,就意味着蛇行者族群会在它死后成为神话族群。这个族群会远超出过去的一切野兽人族群。
另一方面,真龙的遗产在一整个野兽人族群中四分五裂,自然也就谈不上长大,更谈不上陷入永恒的静止了。这正如卡萨尔帝国的皇室血脉。然而卡萨尔帝国只是一场真龙之梦,需要苏醒才能掌握力量,蛇行者却无需如此。
不得不说,和老米拉瓦比起来,血骨这张椅子上坐着的人是更有智慧。
米拉瓦反握住地上的长矛,不顾烧灼的强光将其用力投出,只见它划出一道致命的轨迹,竟从山底往上径直贯穿了穹顶。那道轨迹比尺规描绘的还要笔直,比整座黑山还要高。它先是带着磅礴的气流撕裂了十多个蛇行者将其贯入穹顶,穿透山峰,掷入燃烧的王都,接着才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回音。
蛇行者始祖高声咆哮,令各个蛇行者往各处散开,凝结着寒冰的巨龙看起来正在破碎,往蛇行者始祖和米拉瓦两个方向崩溃解体。
不止是米拉瓦,蛇行者始祖也盘踞在穹顶变得越来越庞大。起初它还是一条虚空中的巨蛇,如今它已然长出了尖爪、拥有了犄角、展开了羽翼,碧绿如玉的鳞片裹挟着虚实不定的蛇身,辉映着被米拉瓦撕裂的穹顶,折射出炽烈的血色红光。
从残忆中坠落的野兽人像蚁群一样涌向米拉瓦,要扰乱他对真龙遗产的争夺。法兰帝国的骑士们刚刚突破野兽的重围抵达此处,见得此情此景,不禁都陷入呆滞。
“为你们的皇帝重夺荣耀!”老皇帝发声高呼,声音如雷鸣般在这片广袤的空间中回荡。
“该帮谁呢......”亚尔兰蒂不禁也陷入迷思。
塞萨尔看了亚尔兰蒂一眼,这家伙似乎很缺乏主体性,总想找个东西去依附,借着其他人的名义行事。“这份遗产四分五裂已经注定了,”他说,“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帮哪边,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分一份,不,是两份。”
“两份?”亚尔兰蒂眨眨眼,“除了我们一言不发的古代先知,还有人也想要?我觉得这东西很危险,装在玻璃瓶里观察还差不多,真要给我还是算了。是你想要吗?“
塞萨尔握住蛇行者的尾巴,不顾它应激的反应缠在自己手腕上,用力握紧。“蛇行者始祖得到了一部分遗产,它注定会死亡,这份遗产也注定会成为它族群的遗赠。问题在于,这份遗赠不会落在先前出生的蛇行者身上,它们这些先行者,将注定会成为后辈的垫脚石。”
“别抓这么紧,先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看向米拉瓦,看向藏在这家伙灵魂中的骗子先知。“现在,你是想眼睁睁看着你的一切都被撕碎带走,还是想用另一个米拉瓦的名义站出来,在皇后亚尔兰蒂的支持、在法兰帝国骑士的冲锋下拿走仍然属于你自己的一份?当然,你得匀给我一份,我会把这些转交给这条认我当主人的小蛇,确保它能凌驾在所有族群同胞之上。”
“你还真是永远都不会失败,永远都会有条索让你抓住爬上去。”骗子先知声音悠扬,“我曾听你自述,说你只是碰巧在所有走向失败的路途里找到了成功的一条,现在看来,这话可不怎么像真的,——这种路到底是你碰巧找到的,还是你扔了条索道强行搭出来的?”
“那你要我说什么?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失败了,封死了,你的遗产已经被抢了?”塞萨尔瞥了她一眼,“没有什么彻底的失败和彻底的困境,无非就是再找条索道扔出去,再试着爬一下,这条不行就换下一条。即使老米拉瓦已经把遗产全都占有了,我们不还是有法子让他再吐出来吗?你是它的主人,别说你不知道怎么催熟自己,让他在立刻长大陷入永恒静止和把东西都吐出来之间选择其中一个。”
蛇行者观察了他一阵,尾巴逐渐缠紧了他的胳膊,“你的话里有真理,先知,我赞同你的看法。不过,你可曾想过,如今真龙的意识就依附在米拉瓦的灵魂中,这份遗赠,我们年轻的皇帝又会如何看待?”
亚尔兰蒂开始升向穹顶时,年轻的米拉瓦也往前迈了一步,他看起来很不想看到老米拉瓦借着真龙的遗产占据优势,毕竟,老皇帝已经占据很多很多优势了。这家伙也想和骗子先知争夺遗产吗?
“米莱......”塞萨尔思索着说,“你是否想过,就这么追寻老米拉瓦曾经走过的路,你只会被越甩越远?他已经占据了这么多的遗产,即使你想抢夺,你也只能和遗产的正主争夺更少的一份,然后你会被抛得更远?”
“我.......”
“你有感觉到战争和冲突之神的气息正在老皇帝身上越变越衰弱吗?”塞萨尔又问他,“真龙的遗产占据他之后,他将不再是赫尔加斯特的神选者。你是想去捡拾他抢夺遗产的残渣,还是想成为唯一的赫尔加斯特神选,用他无法再走的路途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