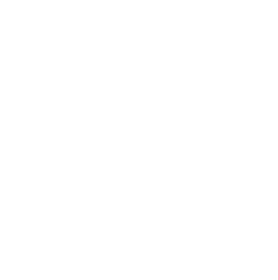雨幕依旧黑暗阴森,但戴安娜精灵般的脸颊和冰肌玉骨落在黑暗中,仅靠着些许微弱的晨曦也显得异常洁白,一度透出些许红晕。她臀部饱满,腰肢细柔,长发如同波浪,靠在他怀里胸腔起伏,就像条沾满雨水的湿漉漉的白蛇。她踮着脚吻了他,这吻和他主动的吻感觉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嘴唇短暂分开,塞萨尔轻吻她的颈子,感到她在他耳边轻叹,用手抚摸着他的胸膛。等他在她白皙的颈侧留下一道清晰的吻痕,他们再次慢慢接吻。他紧紧环住她的腰,将她拉近自己,她也用两手扣着他的脊背和后脑勺,带着发烫的呼吸回应他的吻。
唇与唇的触碰逐渐变得漫长,后来因为吮吸和噬咬变得发痛,稍微一碰,就让人浑身颤抖。他含住她黏滑的舌头品尝,缓缓吮着,然后是轻轻的咬。他感觉她用灵巧的舌尖轻舔和抚慰他发肿的唇瓣,于是他也舔舐她的唇瓣,接着在彼此的唇间触碰,互相轻挑,紧贴在一起摩擦,渗出丝丝缕缕的晶莹唾液往下滴落。
等到嘴唇分开后,戴安娜喘了好久的气,胸腔起伏不断,心跳众筹群四伍⑥壹贰七⑨四零也难以平息。他起初只是屈膝吻她的颈子和锁骨,但她把他越抱越紧,双手紧扣他的后脑。他鼻尖滑动,触碰到她衣襟之间的柔软罅隙,轻轻探入她的衣物。他用嘴唇拂过那片软滑的嫩肉,牙齿也落在那处柔韧发硬的地方,先是亲吻,然后是轻咬,接着是满带着渴求的舔舐和品尝。
等到她止不住地把腰弯下时,她已经满脸潮红,身下湿漉漉的一片。若不是露台上大雨倾盆,只怕会给人发现异状。
“要我抱你回去吗,大小姐?”塞萨尔轻声问她,“就当我是我把多要的一部分还给你。”
“你要的可太多了,野蛮人。”戴安娜徐徐呼吸,“以后我们接吻,我也要给自己准备一份菲妮经常用的术法,因为谁也不知道你会顺势做到哪一步。你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矜持感和最没有分寸的人。”
“那可不一定。”塞萨尔吻到她裸露少许的肩头上。
“什么不一定?”
他把双唇从她肩头上移开,凑到她耳边轻声说,“我是说我们俩可不一定不需要孩子,你说呢?”
戴安娜的心猛得一跳,似乎在恢复正常之前停摆了好半晌。
塞萨尔挽着她的腰扶她下去,到了试验场的门前后吻了下她的柔唇,权当告别。等到她缓过了气,塞萨尔再次把嘴凑到她耳畔,“虽然社会契约上的爱情不一定要有子嗣,但我猜你口吻里的家族多半是要的。你是更在乎自己的孩子也许会成为学派的牺牲品,还是更在乎家族和血脉的传承,这我不知道,但无论哪种,都随你高兴。只是如果是后一种,到时候,我们可能就得多保护一个人了。”
“你想得太远了,萨沙。”戴安娜柔声说,声音轻的像是呼吸,“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你站在结婚典礼上呢。”
“我也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
“我会未卜先知。”她回敬道。
......
虽然很想巡视城防,但今天黑得过了头,塞萨尔决定还是先干些夜晚该干的事情。他迎着倾盆大雨走出城堡,穿过大半个要塞,沿着泥泞的土路往下,终于走到了古拉尔要塞的监狱。
大雨稍稍了缓解的奥利丹北方的闷热,然而刚走进监狱,走下台阶,塞萨尔就想回去淋雨。从一侧的刑讯室传来一股恐怖的窒热,汗水、焦炭和腐败的血肉混在一起,闷得让他一度有些头晕。
他拧了拧咽喉,看了眼若无其事地狗子,心想这家伙究竟有多耐热,但他想不通,于是他脱下上衣,扔到一旁,直接赤膊走了进去。
塞萨尔就着火盆烧灼的光打量刑讯室,分辨出了胖瘦两位拷问官。在拷问官面前的,正是他来要塞时就关押在监狱的犯人。
这是名很奇妙的犯人,看着颇为从容不迫,哪怕倒吊在囚室的天花板上,也顶着一张毫无波澜的脸。两个拷问官在任何囚室都是恶魔,但在这里却满头大汗,神情饱受折磨,其中那个胖拷问官已经是在应付差事了。他把烙铁烫到了犯人的胸口,费力地挪了挪,看着像是劳累到半夜的油漆工在刷墙。
塞萨尔看到犯人毫无反应,皮肤滋滋作响了一分多钟,散发出一股焦灼的肉味也半点反应都无。与其相比,拷问官却累的够呛,最后他连尖端烧红的铁棍都举不动了,把烙铁往火堆一扔,就坐在长凳上抹起了自己脸上的灰和汗。
这人一边擦汗,一边哀声叹气,看着已经想瘫在椅子上不动了。
“我完全搞不懂从北方来的囚犯,这位大人。”旁边那名瘦拷问官开口说,“骑士团把俘虏往这一扔就不管了,却非要我们问出点东西来。您来说说理,这是人能办到的事情吗?”
“你们在这做无用功有多久了?”
“至少也有一个多月了,大人。”瘦拷问官说,“骑士团不许我们把人弄死,所以我们只能看着动手,匕首、尖针、水刑、烙铁、用绳索拉拽全身骨头,老师傅教我们的我们全都挨个试过。上完了刑,看着奄奄一息没反应,等我们眼睛一闭一睁,一夜过去,这人就变成了昨天还什么刑都没上的样子。说实话,我觉得就算把他给杀了,等我们眼睛一闭一睁,一夜过去,这人也会莫名其妙地活过来。”
伤势痊愈?看起来不像,那是什么?听起来像是在反复回溯,——肉身的时间恒定在某个时刻了?
“你觉得这人需要谁来处理?”塞萨尔问他。
“法师,大人,或者就是司祭,哪个神殿都可以。”瘦拷问官说。
“骑士团是从哪弄来这么一个俘虏?”塞萨尔耐心提问。
“那时候骑士团在哪打仗来着?”瘦拷问官咕哝起来。
“去北边的丛林追山匪去了!”胖拷问官咳嗽着说,“我真不知道他们对一伙山匪哪来的这么大兴致,拿他们的人头冒充帝国士兵也得有人信吧?不如去北边找个村庄把不是黑头发的都逮住砍了,不比这法子更有军功?”
“你们觉得是那伙山匪有问题,还是北边的丛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