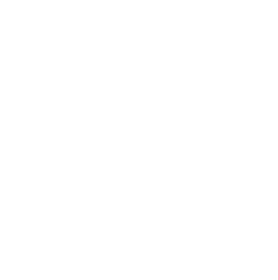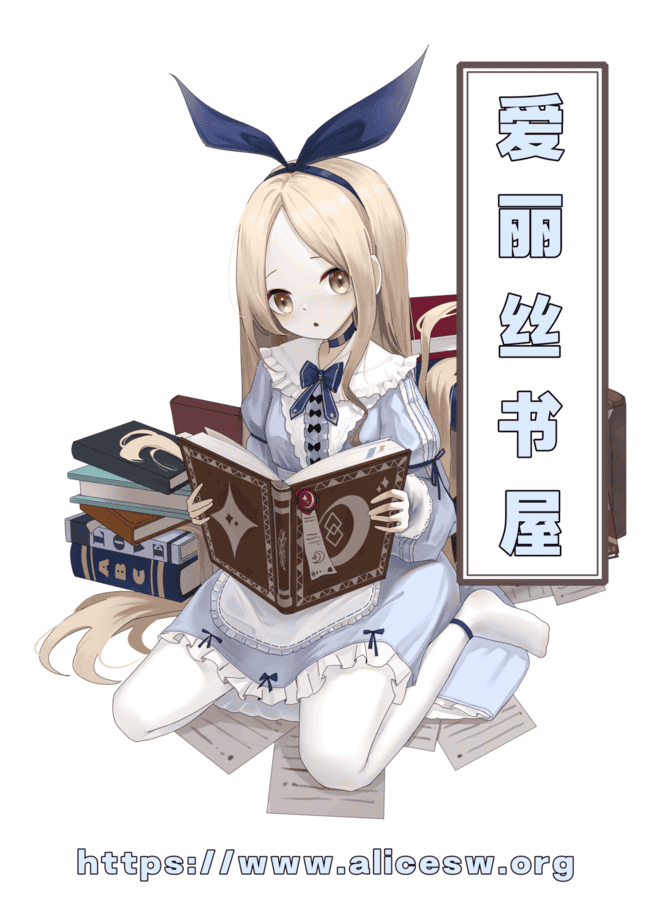......
戴安娜本来以为,没能提前察觉远方的法术就是她今天最大的失态,没想到现在才是。她睁大了眼睛,一时竟然没反应过来。世间万物本无界限,钢铁与血肉亦无分别。先祖的密文忽然得到诠释,就像尖针扎在她手心一样令她手指发麻。
这密文不止是在描述阿纳力克的印记,更是在描述上一个纪元最受人恐惧的仪式。
但是,为什么是他?她在学派的导师给她传来密信,指名塞萨尔此人。但导师只告诉了她一人,未曾知会学派,此事又有何深意?
她在犹豫,先祖密文上支离破碎的言语忽然就产生了联系,得到了实证。
她该把此事知会学派吗?戴安娜知道,只要学派收到她的消息,他们就一定会把此人控制住。他们会扒光他的皮,把他的骨头和血肉也剔干净,把他隐藏在灵魂最深处的秘密都挨个挖掘出来。上一个纪元的知识对各个学派法师意义发凡,毕竟,也只有法师会叫库纳人先民,而非受诅咒的弃民。
烧到焦黑的盔甲像皮肤一样附着在此人无皮的血肉上,拥有了活性,裂开的面甲好似狼之口,随着呼吸缓缓开合。他的胸甲亦贴紧了腹腔,分明是金属材质却起伏不断。他朝戴安娜转过身,抬脚跨过了地上一具烧成炭的残尸。
上一个纪元的幻影,行走在世间的非生非死之物,受诅的......
戴安娜心知此人已经跨入第三视野,无法分辨出人类个体间的微小差异,因此,他也无法分辨她和山下的骑兵有何区别。这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死亡正在靠近,但是她没有后退。她强迫自己从记忆中翻出另一段密文,迅速在胸前勾勒出象征着库纳人祭司的印记。
那幻影停了下来,伸出手,把锋利如兽爪的手甲点在她胸前漂浮的法印上。
“不管你认不认得它,幻影,现在都是我让你恢复了神智。”她朗声说道,“根据古老的契约,保护祭司是你们的应尽之责。”
钢铁下的血眼盯着她,仿佛没听懂她的话。
“这个战场已经没救了,”戴安娜继续说,她已经做出了决定,“骑兵冲锋已经无法阻挡,你也不可能站在这里杀光战场上的所有人。先不说有来历不明的学派法师藏在暗处,叛乱者的火炮多半也已经在路上了。只要你维持身体不动,并且屏住呼吸,我就能带你当场消失。”
钢铁包覆的幻影转过脸去,看向山坡下的战场。
所有阵线都已经无法分辨,轻骑兵还在利用地势和重甲骑兵做机动,但也只能困在山林中迂回,大量骑兵正试图从两翼包夹他们的去路。步兵更是无法指望,要么正在溃逃,要么就是在即将崩溃的路上。
这些人已经完了,戴安娜想,尽管利用高明的战术袭击了走私部队,还利众筹群四伍六一二柒⑨④零用火炮对叛乱军造成了巨大杀伤。但是,他们终究无法抵挡这等规模的冲锋。要不是叛军想回收火炮,刚才在烈焰中烧毁的就不是这段山坡,而是整个火炮阵地了。
“如果你还在为你生死难测的道途深感痛苦,那很好,我就是能解决你一切问题的人。”戴安娜强调说,“别问为什么,我读过的文稿里,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描述可以堆满一整个房间。”
她说的有些急促,因为重装骑兵已经冲过山坡,冲过完全溃逃的步兵,像海浪一样席卷了过来。他们直扑山坡上的指挥所,直扑他们而来,她不可能挡得住这么骑兵,哪怕刚才使用了战争法术的法师也不行。
这么近的距离来不及做任何事,只能逃。
“你还在犹豫什么?”她再次发声。
“不,”此人忽然开口,声音嘶哑而低沉,“指挥所不能沦陷。”
“它在被火烧尽的时候就已经沦陷了!”戴安娜抬高声音,“就算你不会轻易死去,但在所有目睹了这一幕的人眼里,它和沦陷又能有什么区别?”
那张狼口撕裂得更开了,手甲几乎不再是兽爪般的轮廓,而是张开的利刃,她感觉整具盔甲都带上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54
群集的铁蹄践踏声越来越响,戴安娜眼看着一批又一批骑兵伸出的长枪从硝烟中浮现,朝指挥所冲来。正是他们的冲锋把步兵线列撞的粉碎,冈萨雷斯提供的士兵实在太少,装备也不足够,士气更是脆弱的可怕,一旦把往日的训练抛到脑后,尖叫着逃跑就是他们唯一的反应。
“你想做什么?”她再次问道。
“你似乎并不理解决定战场胜负的是什么。”他道。
“你......”
铁甲映着晨曦越发靠近,骑手们齐齐发出令人胆寒的战吼,汇聚成一片狂热的咆哮。塞萨尔示意她往他身后退去。
“你很快就能明白了。”他说,“有些事情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容易理解,这位祭司大人。”
接下来几个呼吸的时间里,此处发生的事情是很让人费解,塞萨尔并不忙着举剑,反而是拿起号角,长呼一口气,瞬间就使号声从指挥所中央响彻了大半个战场。
四下里目睹了先前法术的士兵都停顿了片刻,很多人的视线都不由自主转了个方向,有些较远处的士兵甚至跳了跳,想看清楚烈火席卷过指挥所以后,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吹响指挥所的号角。
第二声号角用更强烈的声音响起,把她的脑袋都震得嗡嗡作响,——这当然不是人类能有的吹息。前排战马受惊的片刻时间,塞萨尔应声跃起,跳向关隘狭窄的入口,像块坠落的黑色山岩一样从半空中跃下。那双铁靴踩中了打头的骑手,先是借着坠落之势踏碎了颅骨,然后继续往下踩烂身体,把战马都拦腰截断,把人和马的死尸都踏进了泥地。
这一幕之惊悚难以形容,只见死尸的残骸在冲击力作用下四处泼洒,破碎的枪盾、折断的骨头和残缺的躯体都飞溅到半空中,形成了一大片污秽的血雨。
戴安娜觉得他现在几乎不能称为人,是寄生在活化盔甲里的血肉。
两侧受惊的骑兵高喊着举枪下刺,塞萨尔却放低剑尖,身子伏地,像头飞扑的野兽般迎着林立的骑枪朝前一跃。只见他掠过一长列骑兵,活化长剑划出十多米长的弧线,而后切断的身体才伴着飞洒的血液滑落各个骑手的腰部,摔向坡地,滚落山崖。
他的动作和姿势很诡异,既像野兽又像人。跃至最后时,他一把抓住了一个骑手的头,踩着那人的身子砸在了地上。待他松手时,骑手的头盔已经顺着手甲的爪印凹陷了进去,挤出大片血浆和脑浆混在一起的黏液。
此时后方的重炮再次发出巨响,可怖的轰击从关隘下的缓坡一直覆盖到低处的古道,仔细一看,竟是炮兵从走私部队的货物里找到了榴弹。视野中一大片骑兵都被横扫而过,像玻璃一样被碾得粉碎,最前排的骑兵几乎是直接炸裂开来,带着焦臭味的碎片四处抛洒。战线的压力稍有缓解,顿时有多支号角围绕着指挥所发出高亢的回应。当初公爵派来的轻骑兵们正在呐喊,在遮蔽视野的硝烟中四处穿行。
号角再次响起,和环绕关隘的队伍相互回应,堵在山道上的士兵都端着长枪朝烧焦的盔甲下刺,散发出坚定和惊恐混杂的情绪。但那家伙并不在意,他跃到人群正当中,手臂起落,挥舞长剑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他用喉咙发出的声音像是恶魔在嗥叫。这人离血肉之躯崩溃几乎只差一步,但那具盔甲约束着他,迫使他维持人形,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像恶魔一样在人群中肆意穿行,像拧碎枯枝一样击碎人体,把血浆和残肢甩上天空,到处都是四分五裂的尸体和横飞的碎片。
而他毫无疑问就是套着人皮的非人之物,现在也许连人皮都说不上,仅仅是类人了。
坡道上的骑兵毫无预兆的退缩了,军官在其中呼喊指挥,命令他们勉强组成阵线往后退去。此时戴安娜却感觉到了法术的印记,在远方汇成了一个明亮的点。虽然常人不可见,但她能察觉那种现实遭受扭曲的异样感。
很明显,由于骑兵突破关隘失利,火炮造成了他们承受范围外的损失,那边的指挥官开始想要放弃货物的回收,转而要求法师直接摧毁它们了。
要对抗吗?战场形势确实有所改变,她多年来筹集军需物资......也许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戴安娜刚思索片刻,塞萨尔已经从坡地跃回到她身边,一具尸体正插在他的剑上癫痫,好似穿在竹签上的鹌鹑。这家伙沉陷在第三视野里,已经分辨不出人类的形体了,多半是看到剑刃上环绕着一团雾就毫不在意地跳了回来,也不管那团雾究竟是什么。“刚才你话里的意思是,”他意有所指地说,“你能带着别人使用传送咒?”
她后退了一步,免得秽物和鲜血溅在自己身上。“所以?”
“带我找到那个法师如何?”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她蹙起眉毛。他这么理所应当地下命令,她反而不想帮忙了
55
。
“那批军需物资里有很多不明材料,对于它们的归属权,我们可以再做商讨。”
戴安娜睁大眼睛,“你以为你在拿什么东西做人情?它们本来就是我的!”
“那这场伏击的缴获也有你的归属权。”
“是吗?但我觉得找到法师也没用,你的人手还是不够。支援部队不可能来了,只靠强撑无法迎来胜利。”
“不,会来。”塞萨尔说,“如果你看到了我也不觉得奇怪,你就该理解事情不止如此。”
“不止如此又是什么意思?”她抬高声音,“难道你还想用秘闻引我上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