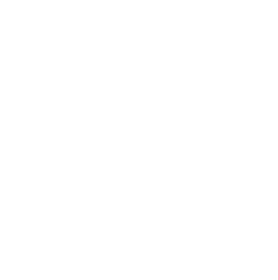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
阿尔蒂尼雅不记得太多事了,但在跌落地面后,她还是沿着深渊蔓延过来的方向不断挣扎,血也不断洒向地面,带着漆黑的火焰熊熊燃烧。她觉得希望就在前方,她需要用那些不定形的黑暗补充自己灵魂和血肉的养料,她瞪着染血的眼睛一步步靠近,用爪子攀着岩石爬过山丘,感觉不过是一个低矮的土坡。
她听到了呼唤的声音,她觉得帝国的子民正在其中呼唤她的存在。那些都是死在战场上的魂灵,他们需要她的......
是的,她记得,任何旧的东西连自己腐烂长毛的地方都要说好,而在帝国,像赫安里亚和克利法斯这些旧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必须拆掉整座破旧的房子,必须检查每一根木头,把所有古老的腐朽物都清除掉。为了这点,她必须往前挣扎,借助她能借助的一切。
如果再不过去,老家伙就又会把她扔进除了宫廷礼仪和梳妆打扮什么都学不会的殿堂中去了,母亲也会命人过来把她带出图书馆了。想到头一次展示自己的能力竟然得到了这种结果,她就想哭,但在用他们的血染红宫廷之前,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必须前进。
但有什么东西拽住了她,让她无法再前行分毫,她竭力挣扎也无济于事。她感觉自己的尾巴被牢牢攥住,缠在一条钢铁包覆的兽爪上,感觉自己被血红色的野兽拖拽着远离了那片黑暗的希望。
帝国的子民还在呼唤她,但她无法回应丝毫,她只看到自己一路洒下的血回到了她的视野中。那些熊熊燃烧的血液意味着什么?是她的诅咒吗?
阿尔蒂尼雅感觉到了血腥味。不知是谁的手指搭在她的尖牙上,任由她咬下,不知是谁的血从她口中渗入咽喉。这血烧灼着她体内淤积的黑暗,让她感到剧烈的痛苦。她想挣扎,但另一只手按住她的后颈令她趴在地上,无法挣扎分毫。
越来越多的血涌入喉中,她瞥见一张钢铁包覆的脸上破碎的盔甲正在剥落,现出那张布满了驳杂胡须的面容。破碎的黑发粘在满是血污的额头,其中是一双俯瞰她的漆黑眼眸。她眼看着他和自己一同变得越来越小,先前低矮的土坡却越来越庞大,最终化作一座巍峨的山峦。
“你的确以你一人之力挽救了当时的战场局面,阿雅。”他说,“不过,你似乎没有能力处理你一手造成的另一种局面。”
“我犹豫了,老师。”
“你可以说的更接近本质一些。”塞萨尔皱眉说。
“我应该更早意识到我该做什么,更早接受那些深渊物质,如此一来,至少要塞不会面对特里修斯的威胁。”
“其它的威胁呢?”
“其它的,我都会......”
“你没法处理。”塞萨尔摇头说,“你也知道,我一直都不是很情愿利用我的道途,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无法处理我会因此造成的灾难性的局面。有太多未知的恐怖和未知的威胁存在其中了。”
“我可以处理,我只是犹豫了,没能争到先机。”
“你小时候会这么跟赫安里亚争论吗?”塞萨尔问她。
“不会,”她说,“我在宫廷一直都很谨慎,直到后来......也许是谨慎得太久想要求得解脱吧。在那次展示自己之后,我就变得更谨慎了。”
“你这回答可真是让我难办,阿雅。”
“我的骄傲和自信未必是来自于你,但你的以身作则一定是把它加深了,老师。”
“那么结果呢,我们要如何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为我们犯下的错误表示歉意?”
她摇头,“战场上的生和死没有表示歉意的余地,我......要塞.众筹群肆⑤陆一贰柒玖④零.....要塞怎么样了?”
阿尔蒂尼雅记起了一些遥远的情景,记起了和特里修斯在黑暗的天空下纠缠的野兽。盘旋的飓风在他们身边咆哮,乌云也卷动着众多可怖的大漩涡,瀑布一样磅礴的洪流从中倾泻而下,使得大地颤抖破碎,一切都变成了四散的阴影。那些飓风冲击着一切,也遮掩了她的身形,让她得以从特里修斯的爪牙中挣脱,从半空中朝着深渊飞掠而去。
真是奇怪......羞愧感来的好快。因为意识到是他处理了一切后续事态吗?
“神殿的人正在和叶斯特伦学派的法师一起收拾残局,”塞萨尔告诉她说,“因为要按莱戈修斯给的法子处理退潮的深渊物质,戴安娜也忙的脱不开身。要知道,她本来想在旁边看着,但她顾及到你的颜面,就把事情全权交给我了。你应该知道自己要接受什么吧,我的公主殿下。”
“是你处理了失控的事态,挽回了一切灾难,你可以决定怎么责罚我。和我本应承担的相比,这一切根本无所谓,我......”
那声响回荡开来的时候,阿尔蒂尼雅长吸了口气。她几乎要记不起刚才的一巴掌落在屁股上是什么滋味了,但她现在只感觉麻木,还有针扎一样的剧痛。见他手还想往上抬,她本能地往后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这只手上包着铁。
阿尔蒂尼雅抓得非常紧,她感觉自己的手指紧紧钳住了他的手腕,可是,她没法转过身不再趴着,因为她的屁股仍在抽痛,恐怕稍微碰一下地就会让她痛苦难耐。
“我还没有准备好,”她勉强喘了口气,开口说,“您至少应该......”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塞萨尔否认说,“而且是你说这一切根本无所谓。“
阿尔蒂尼雅几乎是喊了出来:“我没准备好挨比宫廷杖责还重的巴掌!”
“也许是因为你刚接受了深渊的洗礼,还一度化身为一头黑龙喷吐烈火,”他又说,“我总不能用打小孩的力道对待你。这不尊重,不对吗?而且也没法让你记忆深刻。”
她放轻声音,“我的记忆已经够深刻了,我想,我们应该回古拉尔......”
“还没完呢,”塞萨尔打断她说,“我在这地方照看了你不止一天了。可能你觉得我们俩很快就变回了人形,事实上我在这地方给你喂了能把一个活人放成干尸的血。期间我让戴安娜梳理了一下事态,列出了你犯下的一系列过错,列成了一个表。我要用我这只手挨个把它们记在你心里。”
“必须如此吗?”她问道。
“至少这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会让你颜面尽失。”塞萨尔说。
“好吧,那您可否脱掉这支铁手套,老师?”
“不,”塞萨尔否认说,“没有这只铁手套,巴掌的力道就没法穿透你的裤装让你感觉到痛了。”
“我不想看到这只铁手套。”她用尽可能委婉的语气说,“宫廷里仗责奴隶都会用木杖,您却用铁的。”
“宫廷里的奴隶可不会洒下一地燃烧的鲜血。”
阿尔蒂尼雅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腕,把自己往起来撑了点,死盯着他,“把裤子扒下来的话就无所谓这只铁手套了吧?”
“这不合适吧,公主殿下。”
“我不相信自己恢复成人的时候衣服还会穿在身上,如果这身衣服是你在我赤身裸体的时候给我套了上来,老师,那这事就没什么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