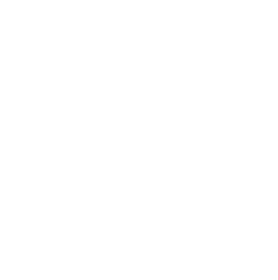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
穆萨里在大帐里看着信使加急传来的密信,不禁有些恼火。
他已经在此召集了各部族的酋长和出征的勇士,也筹备好了行军的物资,出征的动员已经做好,在动身以前,部族勇士们或是聚集起来饮酒起舞,或是在分别前抱紧自己的妻子彻夜活动,想再弄出个孩子。有人大喊,有人高歌,有人不停怒吼,所有人眼中都闪现出对即将来临的战事的期待。他们是萨苏莱人,每个男人都是可以上马作战的勇士。
这么一个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刻,法兰人送来密信,竟然是再次嘱托他们谋杀一个不名一文的私生子?
真是个侮辱。他们把萨苏莱人出征当成了什么?宫廷权谋和贵族私斗的延续吗?
“王后最疼爱的弟弟死了。”信使在桌子那边对穆萨里说,“我们再次要求你,穆萨里酋长,杀死塞恩伯爵唯一的儿子。”
“你们的王后有更具体的指示吗?”穆萨里把信件扔到一边,继续翻桌上的各部族汇报。他正在统计各酋长的要求,有些部族受灾严重,需要大量粮食;有些部族定居在矿区,需要开采铁矿的奴隶;有些部族工匠快断代了,需要补充冶金的工匠;还有些部族的女人只够给酋长和少部分勇士提供纯血萨苏莱人后代了,如果不能掳掠法兰人当部族战士的妻子,他们就会出兵去抢其他部落的妻子和女儿。
“你们要把此人的头颅寄送到王都。等塞恩下了大狱,王后就会把他儿子的脑袋拿给塞恩,当他死前最后的饯别礼。”信使传话说道。
堂姐杀堂弟还要拐这么多弯,也真是难为法兰人的王后了。虽然法兰人也不区分堂表就是。
穆萨里看着信使边说边摊开一张卷轴,展示给他看。这是副惟妙惟肖的油画,画中清晰描绘了一名年轻男性的形象。此人正站在城堡前的庭院中和一个老人对峙,看着发须
8
乌黑,眼眸同样。比起法兰人,油画中心的年轻看着更像是萨苏莱人,也许,就是那边的城主和萨苏莱人的女性诞下的种?
萨苏莱人和乱石渊南北方边境的其他民族常有通婚和掳掠行为发生,久而久之,也就把他们相貌特征散了出去。在大草原上,也有很多掳掠来的女人怀了萨苏莱人的种,生下一些当不了酋长但能当个普通牧民的孩子。
“鉴于你们没保护好埃尼尔。”信使续道,“我们无法完全信任你。”
难道不是那个宫廷出身的蠢货自己要绕道去刀锋山吗?他们死了一个经历过库纳人考验的剑舞者老战士,他们才更应该谴责他!
“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去办这事?”穆萨里质问他,“你们的间谍能潜伏在城堡的庭院里画出这幅画,却不能对付一个不名一文的私生子?”
“因为间谍只是间谍,间谍的职责是传出我们想要的消息。”信使把油画交给穆萨里,“而且,这是你们没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这个塞萨尔逃出城堡的时候,你们就该杀了他。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你们所谓的剑舞者,既不能杀死一个私生子和他的侍卫,又不能保护......”
“得了吧,”穆萨里打断他,“你们自己声称老城主只是个缩在龟壳里的废物,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早知道他有能力派一支队伍杀了她的傻弟弟,你们干嘛还允许那蠢货去诺依恩大放厥词挑衅城主?我是按你们的要求提供的保护,——你们的要求,听明白了吗?那么是谁允许这个埃尼尔去诺依恩的,是你们的王后?还是你们王后的父亲?你要不要把他们俩挨个问责一遍?”
有那么一阵,信使没说话,脸也僵硬得像石头。“关于塞萨尔此人,他和他的父亲有矛盾,如今处于希耶尔神殿的大祭司保护中。我们尚不明确他是否会和神殿人员提前出城,要是他会,我们会自行解决此事,要是不会,我们希望你们尽可能让城内陷入混乱......”
这话题转移的可真是太僵硬了。
穆萨里死盯着对方:“好配合你们派过去的刺客?”
“我们当然会派刺客过去,但是,恐怕没有刺客敢袭击神殿大祭司落脚的住所。”信使低下头,“你们的配合必不可少。只有制造出足够的混乱,才能找到趁乱杀人的机会。”
“我们自然有法子让诺依恩陷入恐慌,但在城内制造真正的混乱,这事最好由你们的人干。”穆萨里往前探了点身,压低声音,“散布谣言、煽风点火、放火烧营、谋杀军官、栽赃陷害,这些事,你们法兰人难道不是干的最得心应手?我会在回信里把这些都写上。如果你们舍不得让间谍冒着暴露的风险多干点事,到时候出了岔子就别来找我。”
“你......”
“不管怎样。”穆萨里坐回自己的椅子,“我了解你们,知道你们都能做什么。既然我在出力,我希望你们也别那么害怕牺牲自己。只要能把事情做到位,到时候,哪怕你们的刺客都失手了,我们也会更有余力处理此人,明白吗?”
......
最初,塞希雅要求塞萨尔自己准备练习用剑的时候,他掏出了力比欧的剑。佣兵队长当时脸色就变了,——这剑的剑身上有几个坑,剑尖也磕掉了,它原本是把很有收藏价值也很有威力的武器,如今看着却像是从战场上捡来的破烂。
在她强笑着问他是谁对这剑下了狠手后,塞萨尔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的冒失。得知此事后,塞希雅一整天都很不高兴。
后来,塞希雅把这柄剑托付给了本地铁匠,并要求修好之后塞萨尔六个月之内不准拿出来,也不准使用。因为,若是在练习时磕出了划痕,或者撞掉了剑柄上的配饰,如此往复一段时间,他一个月支付给铁匠的维修金会比他付给塞西雅的薪水还高。
“今天用我从铁匠那弄来的钝铁剑练习。”塞希雅丢给他一把沉重的钝剑,“你碗力和体格不错,挥钉头锤也挥得像模像样,所以我决定直接跳过木剑了。”
“因为木剑太容易断了?”塞萨尔掂了掂手里的单手剑,剑身两尺半,两侧未开刃,剑尖那头还扣着扁平的木套,以防练习时戳伤对手。
“因为诺依恩按箱卖木剑的家伙坐地起价,我不想再浪费钱了。这个答案够实际吗?”说到这里,塞希雅又补充了一句,“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按箱买木剑吗?”
“呃,我不知道,老师。”
塞希雅对他示以微笑。“正常来说,一个学员一天弄断一把木剑都会挨骂,你却一天至少弄断三把,你知道这么训练我要买多少箱木剑吗?你继承来的遗产又够花多久?花完之后你要怎么办?”
“呃,先把给您的薪水欠着?等我赚回来了再给您填账?”
“我先把你的狗嘴填了。”
接下来,塞希雅开始板着
9
脸让他练步法和架势,让他用四种不同的防守姿势招架她的进攻,简称换着法子当靶子挨她的打,一刻不停。
和野路子出身的白眼、力比欧不一样,塞希雅的动作姿势很有章法。使剑时,她会让他注意她的前进步,并点出紧跟着前进步的突刺,剑被架开时,她也会让他注意她的后退步,以及忽然用背部带着手臂往前的推刺。她的前进步有很多种,有时候跨步直线往前,有时候带着滑步,有时候带着屈膝,有时候又是跳步,后退时更加复杂多变。
等他挨打挨得已经身体和精神双双不适了之后,塞希雅划着圈直退一大步,“你觉得憋屈了?想进攻就上,你都挨了这么多天打了,别扭扭捏捏。”
塞萨尔确实很想,闻言立刻照办。他屈膝滑步上前,右手的钝剑跟着往前突刺。塞希雅一边招架,一边后退。因为他今天用的是钝剑而非木剑,比寻常单手剑更重,她招架时看起来要使更多力气。虽说这东西不会真正刺伤或划伤人,但足够用力,也能当一把势大力沉的铁棍子。他憋足了劲想要她吃点亏,就是想报她借着练防守的机会连续数天欧打他的仇。
塞希雅继续后退,前脚却踩着不动,只见她膝盖弯曲,看着就像坐在椅子上,反手一剑就撩了过来。她这剑自下而上,若是剑尖划过喉骨足以让人当场毙命。塞萨尔全凭本能架开这一剑,把剑锋扫向一侧,虽然震得虎口发麻,还是强撑着继续上前,靠势大力沉紧逼过去。他持剑下劈,接着又是一劈,好像在抡斧头砍柴,塞希雅不得不往右侧挪了两步。这一回,她用上了手臂的护手挡剑,但冲力仍然震得她步伐往后撤,直至退到院墙。
见她退无可退,脚步不稳,塞萨尔立刻往前突刺,但她忽然一个滑步屈膝往前,身子稍矮,迎面撩出一剑把他这一刺架开,震得他虎口剧痛,钝剑竟然从手指间飞了出去。接着她肩头猛撞在他胸口,右脚踩在他两腿之间用力一拐,他立刻脚步趔趄失去平衡,当场屁股着地,痛得仿佛摔成了三瓣。
“哎呦!”
上了塞希雅演技的当之后,他脱手的钝剑飞出了好几米,跌在地上当啷当啷直响。他也摔得头晕,直感觉眼前发黑。
她抬右脚踩在他胸口上,把他踩得躺倒在地,钝剑用木头裹住的剑尖也顶在了他喉咙上。“如果我踩在你身上让你感觉受辱了,”她说,“你就来跟我解释一下,我教了你三天的脚步和下肢平衡,你为什么一进攻就忘了个一干二净?”
“你可以多踩一阵,你想怎么踩我就怎么踩我吧!”塞萨尔躺在地上哼哼唧唧,“我摔得头晕,要多想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