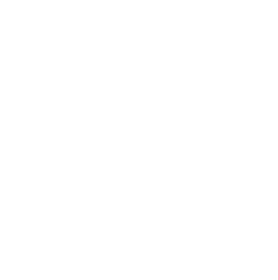塞萨尔感觉世界混乱不堪,四处都弥漫着斑斓的色彩和污浊的血腥味,好像有人在他头顶打翻了油漆,而他正身处水下,眼看油漆扩散开,浸染了水底每一条街
75
道、每一栋建筑和每一具尸体,在水下构成无数扭曲的光与影的轮廓。尸体的手臂纷纷向天空伸展,手指佝偻弯曲,手臂皮肉剥离,如同绝望的信徒在祈祷。
他不断杀死冲过来的士兵,直到站着的仅剩下他和无貌者,还有一个面孔受了火烧的征召兵。然后,他才发觉,诺大的厮杀场,竟然没有哪怕一个人因恐惧而退却。
濒死的重伤者在脚下翻滚挣扎,嘶吼着听不清的话语,好似意识不清的醉汉,哪怕快死了还要辱骂和诅咒站着的人,亦未感到一丝痛苦或恐惧。他感觉一切都被污血抹滑了,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人们的精神,此情此景已经怪诞恐怖到了极点,但远方街道还是有更多人冲来。
赤裸上身的剑舞者在远方对塞萨尔大喊着萨苏莱人的语言,虽然从未听闻过,但他觉得是“邪魔”的意思。阴霾密布的血色天空下,更多草原人好像是凭空显现一样冲出磅礴的暴风雪,朝他们围聚拢来。那个面孔受了烧伤征召兵似乎情绪受了感染,发出咆哮,结果立刻就被一支大箭射翻在地,倒在血泊中。
这人是谁来着?
尸体烧伤的面孔让塞萨尔颇感熟悉,也许是因为意识越来越模糊不清,他记忆也有些混乱,许多东西如同隔着一层雾,看不清晰。然而紧跟着,他发现有抹幽魂一样的血色从尸身中浮现,和兽爪产生了诡异的共鸣。
此人是这条街上最后一具倒下的尸体,看起来附近现在除了塞萨尔,所有人都死了,而一件预备已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那些幽魂就汇入了他在地上四处流淌的影子。
塞萨尔身形晃动。他感觉有种隔膜似的东西忽然碎裂了,他发现自己的视线在一瞬间延伸开来,视野中的一切都变得极度紧密,就像他在半空中张开了密密麻麻的眼睛,藏在无数看不见的缝隙里窥伺四面八方。
每一枚眼睛所见的视野都极度清晰,仿佛把多到足以覆盖整条街道的眼球贴在物体表面去凝视,让人想起攀附在海龟壳上的藤壶。他视野中的一切都因此变得极度致密,并在多个视野重叠之后变得更加繁复、更加致密了。
这种致密让人觉得痛苦不堪,思维无法承受,大脑也一片混沌。他不止是在看他者,还在看他自己。他在自己的视野变成了一张蜷缩展开的人皮。
菲尔丝用力抓着他的肩膀,说着听不清的话,但塞萨尔根本无力回应。他踉跄避开投往自己身体的箭矢,却发现自己脚步快得匪夷所思,感觉是在他四处蔓延的影子上滑行,一步就退入大量建筑构成的迷宫中。
事情越来越诡异了——难道这一切真是无法避免的吗?
他本来可以从矿道的路逃跑,可他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要跟已经注定死于灾厄的人站在一起战斗?为了情谊吗?他们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什么情谊。那难道还能是道德戒律吗?当然,也许他确实是放不下自己身为人的很多东西,本以为这能拖延他走向疯狂的脚步,但如今看来,放不放得下,最终也无法影响任何事。
意识到这点,塞萨尔感觉自己的头脑更混沌了,那些致密繁复的视野也更贴合他的思维了,力量在他身上涌动,好似要他挣脱自己的皮肤破体而出,要指挥他把这座城市都献上屠杀的祭台,满足他对血的渴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应该约束他,他存在的意义.......
“小心萨满!”菲尔丝叫道。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晚了,金色光线勾勒出整个街道血腥的轮廓,只一眨眼间就自地下和墙壁中刺出。无形无质的射线穿过有形质的物体,划出不可阻挡的轨迹向他围聚拢来,比尺规做出的更加笔直,比灼烧的烈日更加刺眼,虚幻却致命。
塞萨尔不断后退,还是被自己刚躲进来的狭窄巷道阻挡了脚步。一束束射线穿透了他的肢体,停留在他身体中,未曾对血肉之躯造成伤害,却让他感到思维迟缓、身躯受制、无法挪动分毫。他的听觉感官中充斥着雷鸣般的尖啸,视野也被磅礴的金光填满,好似有一颗颗正午的太阳环绕着他的身躯烧灼。
雷鸣般的尖啸越来越响,压迫着他的意识和感知,一排排凶悍的草原人战士也在巷道两端出现。他们推倒建筑,劈碎大门,砸跨墙壁,朝他射出致命的箭矢。塞萨尔感觉他们简直是变成了海潮,用长矛和刀剑汇聚成了足以淹没一切的巨浪。
忽然间传来了不起眼的枪声,闪亮的金色光线崩断了,好似泡沫忽然破裂,带着交错的光和影消失在血腥的屠场中。但那名追杀他一路的剑舞者已经接近,此人目光清明至极,无喜也无悲,未受周遭氛围分毫影响。插进塞萨尔血肉的箭矢正被往外推挤,一支支从他身体脱落坠地。
“我们有这么大仇吗?”塞萨尔用诺依恩的本地话
76
问他。
“过去也许没有,但现在很有必要。”剑舞者身份地位比其他草原人更高,所知也比只懂萨苏莱人语言的部族成员更多。
“因为什么?”
“因为你背负罪孽的身份。”
“谁没有罪孽呢?”塞萨尔感觉菲尔丝在低声诵咒,他身体里残留的金光正在被驱逐。“这座城市难道不是你们的罪孽吗?”他问道。
“这不是一回事。”
“凭什么不是一回事?倘若罪孽不是用行动和结果证明的,难道还能是用尚未发生之事证明的?”
剑舞者皱了皱眉。“你是名智者。”
“那你能稍微对智者抱有一点敬意吗?”
“你的刺客也并未对我们的萨满抱有敬意.......而且,何不看看你现在的相貌呢?”
塞萨尔当然知道是狗子杀了他们的萨满,就凭这家伙没有常人认知下的灵魂,不受任何不对现实直接造成伤害的法术影响。他自己现在长什么样,他当然也知道。他满身都是撕裂的豁口,不断喷吐着血雾,形如道道狭长的裂隙连结着另一个受诅咒的世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忽然就是一剑往他头顶劈下,快得根本无法格挡。这名剑舞者比塞萨尔更擅长找空隙,或者说更擅长偷袭,趁着他分神的片刻时间就要一击毙命。塞萨尔迅速后退,身体掠过之处甚至留下了一道血腥刺鼻的雾状暗影,可他还是被紧跟着的一脚踹得飞到半空,砸穿了泥土墙,滚了一圈又一圈。
这一脚几乎踹烂了他的腹部,痛得他感觉肚腹里的内脏都烂成了一团。虽然菲尔丝跪在一旁,抓着他的胳膊不断往起来拉,不停诵咒给他的身体注入力量,但他还是起不来。他身体痊愈的速度完全追不上剑舞者接近他的脚步,刚支起一条胳膊,那人刻满纹身的巍峨躯体已经笼罩了他俩。
挥剑的时候,这家伙全身的纹身都在发光。
在塞萨尔以为自己要毙命当场时,一支玻璃瓶忽然砸了过来,在剑舞者持剑阻挡时直接炸开了大片呛人的火和烟雾,覆盖了整个房间。炼金炸弹?他下意识想到,再想到这地方是狗坑,应该就是地方黑帮非法保存的物件。
他晃了晃晕眩的脑袋,拉着菲尔丝的胳膊想往起站,接着就见一个人影举着砍柴斧朝剑舞者跃了过来。他并不知道是哪的人影,因为他完全分辨不出烟雾中的气味,只知道是躲在这儿的居民。
不过他也知道,冒然朝剑舞者冲锋肯定是自寻死路。下一刻这人就被一脚踹飞了,撞在几米外的梁柱上,瘫软在地,呕出大堆带着内脏碎片的鲜血。草原人的战士正在往缺口处涌来。
“我为那个试图给你解围的傻瓜深感遗憾。”剑舞者瞥了一眼瘫在房间角落半死不活的人影,“但分不清谁才是背负罪孽之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时候忽然从地底传出了声响,不像萨满的法术那样充满光辉,反而像是蝗虫在嘶鸣,像是无数生灵在哀嚎。诡异的词句在铺满尸体的地面升起,在半空中盘旋不止,让人心生恐惧和不安。塞萨尔感觉那些从他身上溢出的血雾忽然间躁动了起来,好像往湖泊投下石子产生的涟漪,在空中迅速扩散,相互交叉,形成道道扭曲的圆环掠过附近的人体.......
突然间涟漪破碎开,扭曲圆环掠过无数人体,使得他们皮肤撕裂,肌肉破碎,血液化作涌泉往外喷溅。而与此同时,剑舞者身上闪耀的光辉竟然熄灭了,好像是被某种无法言说的事物给否决了。
对方这才转向涟漪扩散的起点,发现有个自己从未注意到的女巫正在操纵溢出塞萨尔身体的血雾。塞萨尔也感到异常愕然,因为菲尔丝低声诵咒竟然不是在恢复他的身体,而是在利用这些来自猩红之境的迷雾。不仅如此,这法术竟然诡异地达成了禁用法术的结果,——好像奥韦拉学派的密仪法咒就是这么诞生、起源的一样。
无法理解的事情实在太多,塞萨尔顾不得多想,只管挣扎着拔出剑,趁着对方体格和敏捷复归常人往前疾冲。对方一剑朝他当胸刺来,但他根本不管不顾,用肋骨迎着他的剑锋卡在自己身体里往前挤,一剑直入对方胸膛,溅了他满脸的血。
这时候狗子也趁着剑舞者不备,一枪射进了他的后颈,破碎融化的铅弹在他骨肉中四处迸裂,剜出一大片触目惊心的伤痕。
剑舞者站不住了。塞萨尔却还能动,抬起一脚踹烂了他的膝盖,踢得他跪倒在地,鲜血从其胸膛和颈项中往外喷溅,顺着他刚刚亮起些许的纹身往下流淌,在地上汇成了一滩。剑舞者扭了下脑袋,看向他的眼睛。
塞萨尔拔出剑,用和这人同样的姿势劈掉了他的脑袋。
......
虽然解决了追杀者的麻烦之后,塞萨尔还是得接近那条濒临疯狂的双头蛇,不过在此之前,他实在很
77
好奇中途发生的小插曲。他往前走了几步,挥手拂开弥漫整个房间的烟雾,在那具半死不活的凄惨人体前弯下了腰。
他勉强能听见一丝呼吸声,但他不知道这人还算不算活着,或许已经不算了,他想。先不说剑舞者的一脚踹烂了此人内脏,刚才那不分敌我的法术就足够摧残一个平凡人的生命和一切了。这人皮肤撕裂,肌肉破碎裸露,不过看起来咽喉没受太大伤,还能发出些许声音。
“你还能说话吗?”塞萨尔问道,感觉自己好像从这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的兴致。他的思维是否已经有些扭曲了?
他只听到了几句嗬嗬声,发现此人是个哑巴。可能是因为视线没落在自己身上,塞萨尔便顺着垂死之人的视线往墙壁缺口外望去,看到了被剑舞者一箭射穿的另一个哑巴,——那名面孔烧伤的家伙,或者说,就是当时那个中年搬运工。
遗传性的失语?还是某天一起烧伤了声带?塞萨尔也不清楚,不过这家人都没法说话是挺明确了。
“你想获得你父亲的遗赠吗?”他柔声问道,感觉自己异常的兴致更昂扬了。
这个看不到面孔的家伙似乎无法理解,但还是麻木地点了下头。
“如果你想,就把自己的胳膊抬起来。”他说。
塞萨尔看着这人艰难地抬起手臂,直到抬至半空。于是他拿出野兽人给他的兽爪,把以中年搬运工之死为分界线汇聚来的所有血色幽魂都抽了出来,汇聚成一团沐浴着整个房间的暗红色幽光。他觉得野兽人给他这东西,是想要他汲取和利用它们,但对方越想他如此行事,他就越不想听话。
既然当时他能用它复苏那名老兵,现在拿它复苏这人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你的父亲还有你所有领里同胞的生命,——我猜是你父亲。”塞萨尔颇为玩味地说,“从今往后,这些人就只存在于这里,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了。你依靠他们活了过来,就代表你承担了他们的生命,继承了他们再也无法走过的路、还有他们再也无法去做的事情。你听明白了吗?”
这人稍稍点了下头,于是他把兽爪搭在这只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