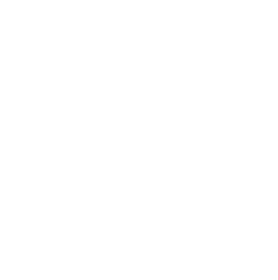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那只是一小部分。”塞萨尔说。他刚想凑近过去,菲尔丝却伸胳膊抱住了他的脑袋,下巴也搁在他头顶上,挡住了他的脸和视线。于是他环着她的细腰把她举了起来,立刻听到一声惊叫。
她实在很轻,不止是抱着没分量,看着也像幽灵,步态和身姿都很轻盈,皮肤则是完全不见阳光的白,脸颊阴森森,眼睛不止带着两圈黑印子,还总被垂落下来的发丝围拢着。最近随着两人日渐熟悉,她对爱欲的兴致越来越少,自己待屋子里对着真知做研究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几乎和最初倒了过来。
这感觉挺奇异,仿佛她当初不过是出于好奇,时至如今,满足好奇的体验已经结束了,就不值得和她多年来的求知欲抢占时间了。但是,她越想逃到书堆里,塞萨尔就越有兴致把她抓出来,叫她回忆当时她是怎么兴致勃勃咬自己的。
等把菲尔丝抱到墙边上,把她紧紧按在挂毯上,他再次亲吻她,并且这次吻地更加专注了,从前胸直到小腹。她的发带掉了,因为本来就是起夜随手挂着,并没绑紧;她搭在身上的外衣也掉了,因为她整个脑袋和身体都在往后仰,就跟被人揪着头发一样;她的头发当然也披散了下来,落得到处都是。
塞萨尔伸手顺着她肩头的发丝抚摸,抚过她往下逐渐变细的背,直到手指落在她向内洼的后腰弯上。她的头发就像小溪一样落下,到尾椎逐渐变细,发梢略略蜷曲弯翘,刚好能抓在手指间,像羽毛一样搔弄她的腰际。
“你今天特别像个没有理智的野蛮人。”她终于缓够了气。
“可能是患得患失吧。”塞萨尔随口说,“我在思考怎么才能骗你跟我去奥利丹。”
“为什么是骗?你想不出好理由了吗?”
“是想不出来。”他说,“我对法师完全没了解,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你在做什么,想用你那东西骗我走?那我必须告诉你,爱人和爱某人的那东西绝对不是一回事。”
“有几分道理。”塞萨尔说。他看着她在自己怀抱里逐渐下落,直到她下腹的终点落在他身上。
菲尔丝低下头,随后抬起睫毛交织的双眼。无言的对视只持续了片刻,她柔滑的胸脯就随着拥抱在他身上挤平了,她的肌肤沾染汗渍,透着湿浊的雾汽,沟壑中亦有汗珠闪烁。她在他怀抱里不
09
住起伏,用手指抓他的脊背,屈着两条腿环住他的腰,双踝也紧扣在他裤带上。
她身上的温度令他意识迷乱,心跳和脉搏似有种奇妙的韵律,能让塞萨尔感到她在爱欲前的矛盾和不安。
最近菲尔丝总是反思自己夜里沉迷于此,却阻止不了自己随着快感变得意乱神迷。就像她刚才还不停抱怨,现在也探寻起了他的口唇,没多久,湿漉漉的小舌头就带着唾液从他口中吐了出来。她的肌肤也逐渐染上一层薄汗,随着胸口摩擦涂抹在两人身上,又黏又滑,让他觉得自己怀里其实是抱着条湿滑的水蛇,扭动个不停。
月亮在窗外漂移,落在她的肌肤上泛着光彩。外面依稀能听到卫兵巡逻,踩出沉重的脚步声。今晚这儿住的都是贵客,巡逻当然彻夜都不会断。他们一边用力干那事,一边又克制着不发出声响。她的脚逐渐屈成弓形,小腿也越绷越紧,直至最后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在手指间发出一声沉闷的回音。
塞萨尔抱着她倒回床头。
“你今天特别可恶。”半晌后,菲尔丝说。
他拿起奥利丹人从他们那儿带来的酒,倒了一大杯,随后瘫靠在床头上。她凑过来抿了口,看起来满意了不少,人也倒了下来,往后坐在他腿上。“好了,”他说,“要讲点睡前故事吗?”
“我不是小孩,不需要睡前故事。”她声明说。
“我是说我们昨天还在讲的那个故事。”他抱着她纤柔的肩头,轻轻揉了揉。
“你是说你打听来的奥利丹的传闻?”菲尔丝嘀咕起来,阴郁的视线往他这儿飘,“你可真会做准备,要是你能给本源学会那边早做点准备就好了。”
“可能是想勾起你的兴致吧,”塞萨尔耸耸肩说,“我想,只要讲我的够多,总能找到什么是你感兴趣的。”
“反正我昨天没听到任何有意思的事情。”
菲尔丝说,又开始抿她捧在手里的酒杯,然后把身子侧靠在他身上,耳朵也贴在了他胸膛上。夜里她听他讲故事的时候,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听他的声音,似乎这样一来,她就不像其他人一样是听他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而是听他自体内发出的说话声了。她说,这样听到的故事声就像血液,从他的心脏流到她心脏里,每一个字都汩汩作响。
“好吧,今天的故事是讲本源学会的内部分裂,以及几个被迫投靠各王国的派系。我们先从奥利丹.......”
“我已经听到你故事里强烈的目的性了。”菲尔丝捧着酒杯小声说,“而且我猜你只知道奥利丹这一个,还是刚打听来的。”
“那我可以把后面的故事欠着,等我打听到其它几个了再续上。总之,故事是这样的,如今正在倒向奥利丹的派系,它其实是一个更古老的学派的分支。在过去某个时代,这个学派因为种种原因分裂了,其中一边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奥韦拉学派。”
“这是能随便打听到的事情吗?”
“奥利丹的乌比诺大公知道很多事,其中一些他不介意传出去......我是说,有目的地传出去。当然说到这件传闻,其实是他的家事。乌比诺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战场名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战地法师,于是......”
“我不喜欢你把故事讲得浪漫过头。”菲尔丝说。
塞萨尔睁大了眼睛:“这也叫浪漫过头吗?好吧,你说是就是。那我这么讲吧,出于政治目的和本人的名望,乌比诺背上了联姻的职责,于是在奥利丹王国和他家族的牵头下,他和叶斯特伦一个生来就是要为派系献身的法师结了婚。”
“听起来好多了。”菲尔丝点头说,“要是这个乌比诺公爵平日里到处找情人幽会就更贴近现实了。我听着你们俩挺有共同语言的,相见恨晚吗?”
“我不知道,呃,这是他的私事。”塞萨尔嘀咕了一声,抚摸着她光洁的胳膊,“总之,联姻的事情很顺利,两边也都有把爱情当牺牲品的心理预期。后来他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嘛,生来就是既要担负叶斯特伦的学派传承,也要担负乌比诺大公的权力、地位和职责。因为这份关系,乌比诺知道很多叶斯特伦的传闻,其中导致他们在本源学会处境不佳的,正好就是这段曾经分裂的历史。”
“这我确实能想象,所以奥韦拉学派就是这么来的吗?”
“我没法说清,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混杂着臆测和推断的故事。事情要从一个法师讲起:在那时代,上个统一的帝国覆灭不久,新生的各个王国都在交战厮杀,从被毁灭不久的土地里诞生的各个法术学派尚未遭遇围攻,对世俗的态度也远比如今残忍。”
“我要补充一下。”菲尔丝说,“过去的法术学派特别残忍,是因为他们的源头往上看是库纳人巫祭,——那是个人殉和人祭特别昌盛的古帝国。如今的法术学
10
派都算是库纳人巫祭的不同分支,各个王国却来自帝国周边部族,每次遇到库纳人祭神都会被迫献出大量子民,送到他们的祭场去。总得来说,嗯......他们反过来围攻法术学派可能也有历史原因。”
“这倒是给我补充了一些缺漏,”塞萨尔思索着说,“在乌比诺的故事里,叶斯特伦学派的分裂,还有奥韦拉学派的发源,其实来自一个带着学派真知出走的法师。据说那个人现在都还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