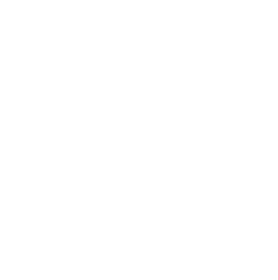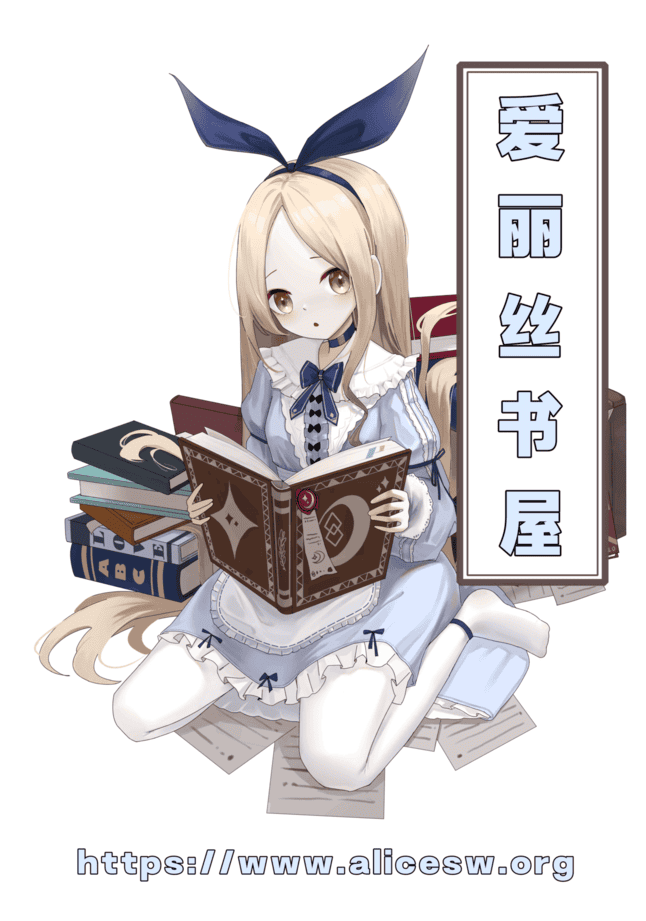......
大片大片军旗在风中歪斜倒塌,仿佛沉没的船帆。戴安娜这才发现旗帜附近根本没人,只是插在那儿壮声势的物件——所以,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她当时预计的还要
49
少。一波又一波重装骑兵冲入林地,冲上山坡,冲向数目丝毫不占优势还轻装上阵的士兵们。
叛乱军的重装骑兵扬起了漫天尘土,声势之浩大,一度让人以为来到了传闻中的北方战场。尽管如此,戴安娜还是可以看到塞萨尔指挥官颇为有序的部队安排。他们的线形阵列拉的更浅也更长了,像个网兜把先头冲锋的骑兵兜了进去,大片步兵竖起了锋利的长枪站在最前,火枪手则分散在长枪阵的间隙中持续射击。
烟尘滚滚中,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接连开火,发出剧烈的轰鸣和震荡,浓郁的硝烟也随之四处弥漫,进一步遮蔽了视野。到处都是号角声、吼叫声、马蹄践踏声以及连绵不绝的枪炮鸣响。尽管冈萨雷斯的士兵们顽强抵抗,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重装骑兵冲进了他们的阵线。
“塞萨尔指挥官的火炮分散放置在整个阵线各处,”阿尔蒂尼雅发声说,“虽然缺少了集中火力,但持续的压制力看起来对长线作战更有效。传言说他对火炮有自己的理论,还为此编纂了一套更精确的使用手册,现在看来传言还是有些保守......你有注意到那些刚缴获的火炮精准的过份吗?他的士兵在随时根据战场形势调整火炮的朝向和射击角度,有时还会让马匹拉着它们调整位置。”
戴安娜斜睨过去,公主殿下的态度比在军事学院听课还要认真。“我不记得有谁写信叫你认他当老师。”她说。
“只是个实用主义的想法而已,没什么值得深究的含义。”
戴安娜叹了口气,“真是不幸,我们接受逻辑学、分析思维和语言辩论的严格训练,竟然是为了拿书里的名词给自己找借口。”
“其实还有数学和几何学理论。”阿尔蒂尼雅微笑着说,“哪怕只为他那套弹道计算的理论,拉他一把也很值得。”
“你也觉得他挡不住了?”戴安娜问道。
公主殿下用合乎礼仪的姿态稍稍颔首,轻得像是在湖面蘸了一下,“目前来看,单靠战场调度,双方的兵力差距已经无法弥补了,即使冈萨雷斯的支援部队正在快马加鞭赶路,也不可能在他们全军覆没以前赶到战场。而且你注意到他指挥所的位置了吗?太靠前了,前线崩溃的太快,骑兵很快就会冲过来。”
如阿尔蒂尼雅所说,海潮般的骑兵像一把尖刀插入战线的心脏,网兜中央的长枪兵最先崩溃。击破他们的已经不能称为土匪,而是和王国精锐一个等级的骑兵大军了。似乎只在片刻间,这批重甲骑兵就突破了步兵方阵,把躲在林立长枪中的火枪兵也冲得四分五裂。很快,这把尖刀掠过之处的每一条线,要么就遭到围困,要么就彻底崩溃。
好在还有尚未崩溃的大片火枪兵竖起长枪,护着后方提供远程轰击的火炮往后撤,也为轻骑兵的迂回争取了一定时间。
尘土和硝烟进一步弥漫,仿佛遮住了整个世界,骑兵们穿着精致的战甲冲上山坡,踏过崩溃逃散的士兵,踩出了满地支离破碎的尸首。即使戴安娜也能看出,那些战甲绝非寻常叛乱军可以概括。弗米尔总督再怎么愚蠢无能,也不可能看到这等规格的骑兵还坚称是土匪乱民。
要么就是他的脑子有大问题,要么就是他的立场有大问题。
重装骑兵冲到了塞萨尔指挥官的关隘前几百步的地方,冲向下一条步兵阵线。此时传来轰隆数声炮响,仿佛是地底生发的雷鸣,震得戴安娜感觉自己脚下都在晃。这是走私部队运进冈萨雷斯的最重要的物资,是需要十几匹马来拉的火炮,看来叛军自己也没预计到塞萨尔竟然让部队深入了这么远,一直深入到了大后方的走私路线。
炮弹从关隘落向人群,顷刻间,就扫过近百名重甲骑兵,不是把他们打下马,而是直接碾过去轰成了血腥的尸块,在尘埃和硝烟中抛向半空中——各阵线步兵接近溃逃的士气似乎回升了少许。
这时候,从另外两侧也出现了横冲直撞的重装骑兵。塞萨尔指挥官的轻甲骑兵只能且战且退,用中距离火枪射击配合炮轰减少对方的人手。虽然他们的灵活性很高,转向的速度也很快,可以最大程度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却遏制不了向着阵地而去的冲锋。
“这几声炮响让他的指挥所更受瞩目了。”阿尔蒂尼雅说,“要是他手头的兵力足够,或者没有为了机动性牺牲这么多,事情也还有挽回地余地。但现在......”
......
大批骑兵仍然从视野尽头不断涌来,冲向他们岌岌可危的阵线,陷入一片混战中。炮弹和火枪持续不断的射击让尘埃混着硝烟四处扩散,使得整个山地都如坠迷雾中,往哪看都一片朦胧。战斗传来的声响震撼着大地,折磨着人们的感官,逐渐让塞萨尔觉得四周不再是剧烈的轰鸣,而是低沉的回音,仿佛是从海螺中传来的大海的浪涛声。
50
又一条阵线被冲垮了,数百重装骑兵冲出崩溃逃散的长枪兵阵线,踏过他们身后成队的火枪手,长剑劈开头颅,长枪扎穿胸腔,把血肉模糊的尸首抛得满地都是。轻装骑兵无法阻挡他们的冲锋,只能迂回到侧翼持续射击,眼看看着他们直扑山丘,直扑指挥所的关隘、战旗和更后方的火炮。
塞萨尔找了块石头盘腿坐下,把长剑抽出,平放在膝,手指搭在剑刃处。
“能做点什么吗,阿婕赫?”他开口问道,“这剑对付不了盔甲,但我不想把奇怪的东西从盔甲缝隙里伸出去。”
“你觉得我们俩关系很好吗?”阿婕赫反问道,“为什么你会心安理得把我当成你的副手,要我给提供你支援?”
“菲尔丝说可以。”
“要是我说不可以呢?”
“那当然是她说的对了。”
“那就把剑从头到尾刺到你身体里,浸满了你的血再拔出来。”她说。
塞萨尔脸色扭曲了一下,但还是把剑抵在自己大腿处的盔甲缝隙,横下心刺了进去,一直穿透到大腿另一边扎在地上,接着继续没入。直到剑柄也沾上了溅出来的血,他才把剑原路拔出。他痛的手指都在发颤,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号叫。
“完成了,现在这把剑是你血肉和意志的延伸了。”阿婕赫说,她的态度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在这东西无法避免的自行崩溃解体以前,你可以随意挥舞它不必担心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