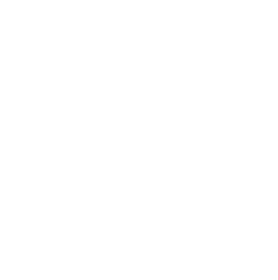塞萨尔等了许久,却发现米拉瓦没有答话。如此看来,类似的事情年少的法兰皇帝经历过许多次,已经知道反驳毫无意义了。只是在对话之前,米拉瓦刚策马赶上索莱尔,看着情绪昂扬,对话之后,他那对光芒闪烁的黑眼眸已经变得无精打采,神情也漠然起来,好像蒙着一层灰。
许多年后的米拉瓦身形高大健壮,面孔经历沙场,带着无法弥合的灼伤,可以让人忽视他白净的皮肤和偏瘦的身子。如今他看着就像个目光无神的少女,纤细瘦弱,脸色苍白,黑色的发丝在风中飘舞,拂过眼睛时,塞萨尔发现这对眼睛里流露出的东西可不止是漠然。
“你也发现了?”亚尔兰蒂微笑着说。
当然,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奇异的,使他整张脸都变得很让人瞩目。当然这双眼睛很大,神采十足,即使在死后,米拉瓦对塞萨尔说起他的理想和信念时也意气风发,仿佛一切阻碍都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它们也很变化多端,比如说现在,它们就闪烁着非儿童的紧张和病态的光芒。
当时在塞萨尔面前,这眼睛里闪烁的是狂热和骄傲,要求他人去服从他的信念、去追随他的理想。
但在索莱尔面前,这对眼睛的神采则是压抑和期盼。因为索莱尔对他的要求他从未实现过,他对索莱尔的期盼也未得到过任何回应,压抑就会越来越深沉,变得像现在这样漠然,蒙着的灰也越来越多。
亚尔兰蒂转着她那双蓝宝石一样的眼睛,最后落在米拉瓦注视的森林中。“这孩子的奇妙之处是,他在盲目效仿索莱尔走过的道路,因此也盲目效仿了索莱尔的习性,但他没能承受的住,已经快要发疯了。”她说。
“然后你就站了出来?”塞萨尔问她。
“索莱尔这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支持她,她往上看只有诸神,她往下看都是视她为神的信众,身边则孑无一人。除了文明的兴衰和族群的希望,她似乎不在乎任何事,所以人们都管她叫圣父,寓意她的精神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限度。米拉瓦效仿她,以为自己应该一个不落的学过来,结果就是他的一生都不拥有任何人,只有他自己,然而人没有寄托又要怎么活下去呢?”
塞萨尔思索着自己看到的一切,“最初米拉瓦把寄托放在索莱尔身上,后来他发现得不到任何回应,灵魂蒙满了灰尘想要发疯,却又找不到其它寄托,你就趁机给他展示了更宏伟的想象。”
“想象?”亚尔兰蒂转过脸笑了,“你说话可真是苛刻,亲爱的,那些历史背后的愿景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是想象呢?”
“因为那只是一个故事,”塞萨尔说,“把一个未长成的真龙描述成所有人的母亲,当作信念的寄托,把库纳人的智者和库纳人的族群概况成弑亲的族群,当作仇恨的寄托。你用这个故事描绘出他的路途,和乡下占卜师用血淋淋的器官、内脏编造出未来的景象没什么本质区别。”
“宗教不就是在这种故事里诞生的?”
“我不否认。”
“就和信徒们自愿献出生命一样,米拉瓦自己愿意受骗。”亚尔兰蒂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袍服难以裹住的胸脯几乎要挣脱出来。“至少我真的了解法术,哪怕我学不会预知,我也可以抓住那些后世的意识,让他们告诉我将来之事。你可知道在法兰人还没学会法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编造的宗教故事?”
眼看她面带迷蒙的微笑,在胸前抱着胳膊,雪白的上半胸脯在袍服的衣襟中晃荡,塞萨尔动了动手指。待到半晌后,他已经一手一个抓住她两团胸脯,几乎只能握住小半,十指都深深陷入到香滑的软肉中。他用力揉搓,拇指和食指也捏住她挺翘的珠子,在指尖捻动,不多时已经听到她迷蒙的喘息。
他吻了她,唇舌交织,再次抬头,一切已经换到一个古朴的石屋中。他看到不知哪个时代的信众们跪在亚尔兰蒂身前,祈求着宽恕,而亚尔兰蒂本人正用另一个声音宣讲。
“这是更早的时代。”她对塞萨尔悄悄耳语说,“至于这个人,就是那个最早在法兰人部落里散布诸神殿起源的人,换而言之,就是我。”
这是个黑暗的屋子,天棚上看似有密布的星空降临到世间,塞萨尔仔细观察,才发现是些闪光的蓝色鳞片,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鳞片。
暗室两旁站着祖先的枯骨对人们低语,要求他们听从先知,但枯骨的遮掩中藏着骨制的话筒,一直连到亚尔兰蒂背后的地下室。塞萨尔循着稻草下的丝线往后看,发现地下室里有擅长改变嗓音的人藏在里面,假装人们的祖先编造宗教故事。
待到枯骨的演讲结束后,有人端着火盆绕着跪拜的信众们走了一圈,黏住枯骨的蜡就给烧化了,然后祖先的枯骨也解体了。
融化了祖先枯骨的火盆被端到一些彩色的宝石背后,光芒透过那些彩色宝石变得璀璨,再穿过一些飘渺的白烟,顿时在亚尔兰蒂背后出现了诸神的幻影,——塞萨尔一直想知道诸神的人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时候。
信众们高呼着先知带给他们拯救,那个古老的亚尔兰蒂也就微笑着伸出手去,覆在最前方衣着华贵的部族首领额头上。
塞萨尔无言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个古老的亚尔兰蒂安抚着众人,呼喊着阿纳力克的罪孽和恐怖,宣讲着她刚编出来的诸神信仰。她高呼出的名字有赫尔加斯特,也有希耶尔,更有很多后世已经遗失的神名。
他站在这位接受膜拜的先知背后,顿时抓的更用力了,好像这样能消解他眼前的一幕一样。那两团胸脯滑腻如脂,珠子逐渐变硬,两圈红晕也逐渐鼓起。他用力把那两枚珠子按进去,陷入白腻的肉中,然后又抓着它们往上提起,用食指挑拨,她脖颈上的晕红顿时更加明显了。
“诸神本来没有名字,”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是神选者在神代巡旅之后把你编出来的人像和名字套在了那些似是而非的存在身上。”
“当时我还很虚弱,也不怎么能用好法术。”亚尔兰蒂对着她面前的信众微笑,“我不得不用了一些奇妙的手段。但这些小手段里蕴含着伟大而深邃的秘密,亲爱的。人们需要迷狂来支持自己,——迷狂,不是一个人的疯狂,而是一群人的疯狂,是所有人共有的疯狂。”
“对他们来说,闪光的鳞片真的是星空,无名的枯骨真的是先祖,还没找回法术的骗子也真的是先知。人们看到烛光穿过宝石和烟雾造成的幻影,于是对着他们想象中的诸神哭泣,谴责那个异神阿纳力克......”塞萨尔喃喃自语。
“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亲爱的?”
塞萨尔握住她的臀部,轻轻一抓,就感觉饱满的臀肉像油脂般滑开,臀沟中已经溢满了汁液。他用左手抚过她渗着水的娇艳欲滴的柔唇,右手挤开她包裹感强烈的臀部,按在红嫩的小孔上。和那饱满至极的圆臀相比,这地方倒是很精致可人,紧紧缩着,俨然是个柔腻闭拢的花瓣。
亚尔兰蒂在他手臂的依托中弯下腰去,小腹略微隆起,纤细的后腰则弯出一个月牙似的弧度,往下逐渐变细,到了臀部忽然翘起,现出一个更完美的圆翘的曲线。内衬的衣物紧贴着她臀部两侧,使得她白而挺翘的屁股更加突出,像是要从织物中溢出一般。
塞萨尔把蛇身从她臀下滑入,挤进她包裹感强烈的臀沟,那地方的肌肤滑腻晶莹,挤压摩擦间比寻常的交媾还要快感强烈。她腰肢轻扭,丰腻的臀部裹着它拧转,带着股惊人的弹性让它越发涨大。惊叹间,她抱住自己饱满的胸脯,裹住他托着她腰肢的手臂。
“谎言和真理并无区别。”她仰头看着他,目光中含着一丝古老的恐怖,“只要追随它的道路就能抵达希望,那就不需要怀疑任何事。”
塞萨尔看着暗室中呼喊着先知的人群,在她臀沟中缓缓滑动,一个失神,已经洒满她光洁的脊背。他喘了口气,蛇头往下,用力挺入她合拢的小孔,米拉瓦显然没有用这地方的习惯,他顿时就感到她精致的眼儿被撑的涨开,越涨挤压感就越强。
亚尔兰蒂不禁阖上眼睛,脸上现出醉人的红晕。待到他抵达深处,那合拢的花瓣已经变成一圈细细的红线,裹着它往里探索,挤压间传来阵阵快感。
这古老的一幕逐渐褪去,塞萨尔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处卧室中,有个和亚尔兰蒂异常相似的女人正站在窗口眺望策马而来的索莱尔和米拉瓦。她怀着身孕,看起来就是亚尔兰蒂的母亲。
他在这使用着亚尔兰蒂身后的美妙,扶起她的身子,转过她娇媚的脸颊,吻在她唇上将她呵出的娇吟喘息含在口中。她耸动着屁股,那圈柔嫩的红线随着它的出入扩大缩小,臀肉也随着他的撞击凹陷弹起,现出诱人的弹性。她伸长了柔腻的舌头,由他含在口中吮吸,品尝她的唾液,胸脯把他的左臂越裹越紧,摩擦间几乎要令他左手酥软得失去知觉。
亚尔兰蒂已经无法说话,她记忆中的母亲却转过身来,似乎她们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就像信众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样,米拉瓦也在我这儿看到了他想看到而且应该看到的东西。”她缓缓走来,“我给了他信念,给了他生活的力量,还拂开了他眼中蒙上的灰尘。你觉得我是欺骗了他吗?既然这是他需要的,我就会用欺骗和诱惑把它交给他。索莱尔给了他现实层面的力量,我却给了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
“不。”塞萨尔皱起眉毛,他分开嘴唇,把亚尔兰蒂抱在他腿上,把手指伸到她唇间,叫她轻轻吮吸起来。她眼中含着情意,就像爱情一样,她对此完全沉醉。“你说了这么多,展示了这么多,但你只提到了米拉瓦,没提到自己。”他说。
“当然,我当年可是为米拉瓦献出了一切,怎么会需要找到我自己呢?”亚尔兰蒂用她的母亲说。她的意识似乎可以分成许多束,一些沉浸在情爱中的时候,另一些可以完全清醒地和人对话。塞萨尔把耳朵靠近亚尔兰蒂的嘴唇,感到了她的柔声呵气,听到她的低语喘息。
他抬起头来。“你没告诉米拉瓦那个所谓的母亲,其实是一只未能长成的真龙。”
“嗯......”亚尔兰蒂的母亲眉头稍蹙,“你从哪来的这么个想法?那不只是库纳人的神话吗?神话故事有这么多......”
“我见过扎武隆。”塞萨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