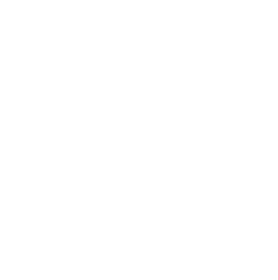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至少你还知道等事了之后再发表感慨。”塞希雅说,她的声音总是充满感染力,“还不错,值得鼓励。”
“你可真会安慰人。”
“安慰人?我只是没有质疑别人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习惯而已。”佣兵队长面带微笑,稍有些揶揄,“你说是吗?刚跟人见了一面就对别人的信仰指指点点的家伙。”
“可能是偏见吧。”塞萨尔自言自语地说。
“你还知道是偏见啊?对别人好点吧,徒弟,不是只有刀剑才能伤人的。你随口几句话就能动摇别人,可要是听者过不去坎,那就是递出
60
杀人的匕首了。”
......
夜里的诺依恩街道冷得过分,寒风在街道上空呼啸,从铅黑色的云层深处卷下片片针状的雪花。积雪覆盖了道路,走在雪厚的地方好像在趟淤泥地,塞萨尔费了点劲才挪到神殿门外,把沾满雪的靴子踩在湿滑的石阶上。
等走到地方,天已经完全黑了,连月亮都看不到。最近这儿逐渐变得安静了,不过,说成死寂也许会更合适。
伤患们本就身体虚乏,加上诺依恩的气候逐渐严酷,围城也让城里收紧了物资供应,便有很多性命垂危的士兵在夜里失去呼吸,再也没法发声了。战争毕竟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就算一场战斗过去了段时间,它还是会在无人知晓的深夜里来找参与者要债。
等大雪过去,从约述亚河引来的护城河会结出极厚的冰,到时候形势又会大变。
似乎是因为塞恩召集了很多人去城堡商讨应对之策,神殿里也不见骑士,只有几个扈从还在看守寥寥无几的病患,正靠在墙边上休息。塞萨尔抵达以后,好长时间都没听到人说话,仿佛是来到了墓室。他在正殿徘徊了一阵,感觉时间的流逝被不断拉长了,直到某个还在守着神殿的修士打破了沉寂。
“你还真是一天都不落啊,塞萨尔大人,这种大雪天谁都不会想出门的。”他侧过脸,看到卡莲修士背着朦胧的月光走了过来。
也许是因为神殿里昏暗沉寂,塞萨尔头脑转得很慢,感觉也半睡半醒。过了半晌,他才意识到是自己看岔了。今晚乌云密布,阴暗无光,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月色。只是她平日里披散的长发被云彩里透出的朦胧月光一照,就会泛出银丝一样的亮光,如今只是微微泛白,也让人下意识觉得是月华从窗户的缝隙中透了进来。
“再过一两天,情况就不同了。”他回说道,“既然还能出来走两步,就该多珍惜珍惜。”
“你看起来不像传言里一样信心十足。”卡莲说。
“今天的传言就像那天广场上的演说一样,都是为了安抚民众才编造出的。”
“我倒是听说事实那部分都没错,确实是你一人拒绝出城作战,因此你手下征召的士兵未有一人出事,也确实是你给那些混口饭的士官教了更精准的火炮射击技艺,因此让他们拿到了功勋。”卡莲又说道。
塞萨尔端详了她一阵。人们在转述一件事时,无论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罢,常常都会掺入自己的主观看法,在她这儿倒是完全相反,——颇像是他前几天夜里描述几何图形构造的遣词用句。
这事很难描述,给他的感觉就是她的身体还驻留在人世间,灵魂却离开了世界,犹如死人离开了活人,并不生活其中似的。
“事实确实是这样没错,”塞萨尔说,“但是,只要换个不一样的讲述人,故事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前些日子里,你从战败的士兵那儿收集故事,士兵们认为我是贪生怕死的贵族少爷,自然不会相信诺依恩为了安抚人心给出的解释。如今你看到领了功勋的炮兵队长,故事是从他们那儿传出来的,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抬高我的形象。”
“那换你来讲呢?”卡莲问道。
“我不擅长骑马作战,当然不可能出城接战,没有其它复杂的理由;教人数学和几何学也只是刚好会,就只是路上随便抓块石头,递到别人伸长了找我讨东西的手里。”
“听起来你觉得自己在受迫。”她说。
“确实是。”塞萨尔耸耸肩,“我就是刚被推上舞台的小孩,什么东西都不懂,只能一边强装镇定,一边在舞台上拉开了嗓子唱我会的唱所有东西,也不管它们合不合适。”
卡莲略微眯起眼睛。“你总是在主张自己的无害和被动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都能算无害和被动,这世界上的人应该全都是没有生气的雕像吧。”
塞萨尔觉得自己被拐着弯咒骂了。
“你有这样语言侮辱过神殿来的人吗?”他也不动怒,直接问道。
卡莲轻微地摇头,说:“他们只是让我失去现实的容身之所,可你却想让我失去容纳心灵的场所。哪怕孤身流亡于荒野和废墟,我们心中仍然能有一片远离尘世的静默,可若是灵魂受了损害,那不管在这尘世的何方就都无法挽救了。”
塞萨尔啧了一声,回说道:“看起来我在你这是罪大恶极了。”
“我说的难道是善恶吗?”卡莲说,“我个人不喜欢用善恶评价他人。我要说的是,大多数人渴望的都是掌握权威,是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军官命令士兵,丈夫吩咐妻子,父母使唤小孩,诸如此类。人们借着权威满足渴望时,需要那些听从他们压迫的人屈膝下跪,表示服从,获得踩在他人头顶上的快感。所以,他们总是要从那个受压迫的人身上得到什么。哪怕杀人犯,也自认为有权掌握别人
61
的生死,要从受害者那儿得到足够的反应。”
“所以?”
“但你不太一样。”
“我有不一样吗?”
卡莲点头,说:“我听你讲了这么久的故事。我觉得,你心里似乎没有权力或者权威这回事,你看起来也不想通过自己优异的能力得到什么,或者迫使其他人对你服从什么。”
“听起来没什么不好。”塞萨尔说。
“但那些渴望权威的人反而没有你这么危险。”卡莲修士的表情波澜不惊,“你什么事都要表达怀疑,怀疑之后就是尝试洞察别人,然后借着你对别人的洞察来表达你的怀疑,动摇他们曾经坚定的信仰、观念和追求。你似乎不想从中得到什么,既不想掌握什么权威,也不想逼迫他们对你屈服,所以在我看来,你就是单纯想要摧毁别人的思想观念。你甚至都不以此为乐,你就是觉得自己该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然后就做了。”
听到这里,塞萨尔不仅想到了狗子,曾经吃下他并和他达成契约的无貌者。他想到了狗子,想到了她的天性,想到了他一度想要扭转的契约,尽管如此,他也不觉得卡莲修士说的就完全对。
确实,他对事物的第一态度就是怀疑,但他表达怀疑,并非是觉得自己就该这么做,而是想发掘出那些无法怀疑的东西。如今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出身地位,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这种身份变化也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他能从前一个身份变成子虚乌有的伯爵之子塞萨尔,当然也能变成下一个子虚乌有的身份。
于他而言,名字和姓氏只是对可以更替的标签,背后的身份也一样。这修士守着她这座再无意义的神殿不走,接受一切命运时,换成他,可能已经在希耶尔的大神殿拿到了骑士身份,接着又从大神殿离开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转场,从神殿骑士当上本源法师学徒了。
卡莲修士看不见他心里涌动的一切,也不知道他暗自觉得他们俩秉性完全相反,如同针尖麦芒。当然了,也许她也曾像这样在心里涌过很多情绪,若非如此,她也不可能对他评价这么多,——她倒是很有洞察力。
塞萨尔摇了摇头。
“我昨天听你说有些伤员不止是患了病,至少不是世俗层面的病。我能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吗?”他问道,“我没在正殿看到你说的那个人。”
“事情涉及到世俗之外的层面。”卡莲说。
“世俗之外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塞萨尔觉得他等着说这段话有一阵时间了,“待在军营的这段时间,我有天晚上梦见了一个面目像是野兽的人。我觉得这是个启示,有些东西需要我去挖掘。”
“你不是怀疑论者吗?为什么相信预言和启示?”
“我以前不相信,不过,最近我觉得我该怀疑怀疑自己这种偏见了。”塞萨尔对她说,接着又开始跟她讲那名随军法师莫名失踪的事情。
他本以为自己需要花点时间来说服她,但她竟然同意了。
“既然围城战不久就要来,”卡莲说,“既然事关你自己的命,那就不用再多说了,我引你过去就好。至少这件事上你没有用心不良。不过我感觉你话里掺着谎,如果以后你还有事找我,我会记着这笔账的。我通常不计别人的账。”
作者的话:两本都写等于两本都卡,三十多小时没睡感觉要精神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