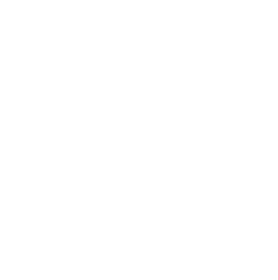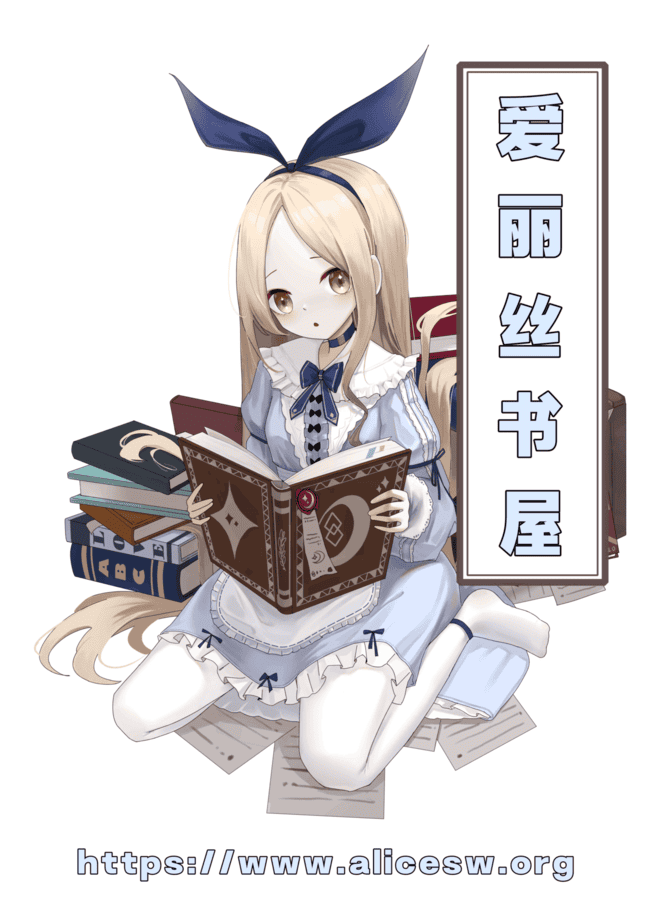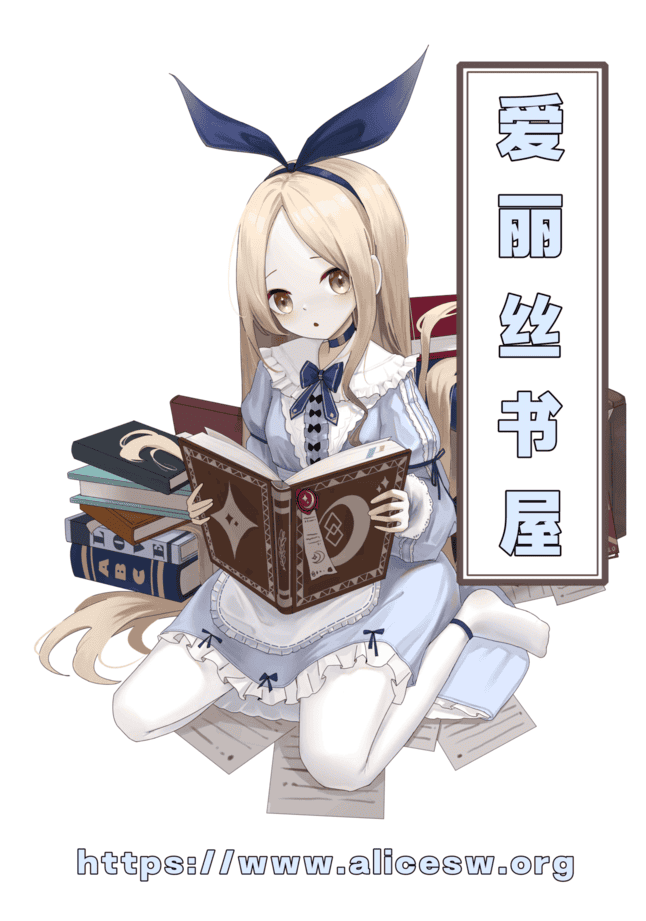这话听着实在绝妙,从许多年前开始,塞萨尔就许下过不止一个誓言了,现在来到此处,自然都已无法实现。哪怕来到此处之后,他对菲尔丝许诺,说自己不会受灵魂腐蚀的影响,时至如今,他也早已无法抵挡那红雾弥漫的异境对自己的侵蚀。
可以说,是伯爵城堡地下的祭台为他开启了新一轮的生命,把他从既定的死亡拉到了摇摇欲坠的悬崖边缘。而比起小女巫一次次从坠入深渊中拉起他的恩情,他本人的誓言和承诺,其实也都是些虚弱无力的东西。
眼前这家伙,救她一命就愿意以命相交,以自己的后半生为他寻找获救的机会。他不自觉地蒙受了这么多次帮助,结果也只能说些虚弱无力的誓言和承诺。说实话,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机会实现它们——以他被迫站在台前的情况,他也难说自己真能如他所说,先往本源学会控制的城市去。
他们从还没修缮的城墙缺口往上走。
“你这话要是换我现在说出来,”塞萨尔说,“就像在白日做梦。”
“我陷在泥潭里的时候,也整天白日做梦,希望自己想哪去就往哪去。”阿婕赫说,“你看着像是头一回发现自己只能做梦。”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建议你往左走几步。”
塞萨尔没注意她这句话,然后一脚踩空,差点被松动的砖石带到城墙底。
“你能预见未来?”他惊讶地盯着她。
“我能感觉到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阿婕赫轻描淡写地说。
“那还好。”塞萨尔说,“至于做不做梦,我以前也在诺依恩的泥潭里白日做梦,想要逃到城外去。后来我结识了很多人,试着借助的力量他们帮自己逃出去,眼看就要成功了。再后来,我有了数不清的机会可以直接走开,但我总不能把我结识的人都像工具一样扔掉,只自己走开。”
“你和太多人走太近了。”
“那你就是太孤僻了,从不接近任何人。”他回说道,“哪怕是你的血亲。”
“经历从古王朝至今无数死者的记忆已经够累了,我没空和还活着的人有太多交集。”阿婕赫说。
“我以为你话里的做梦只是那条蛇的梦。”
“它还小的时候就在汲取死者的记忆,越积越多,在它的意识里汇成一片汪洋,但它本身只是一滴水。”
塞萨尔觉得那条黑蛇到死也不可能清醒过来了。
“所以你其实已经有一个模糊的路线图了。”他换回先前的话题,“你外出旅行,与其说是探索未知,不如说是重历过去的脚步。”
“这场旅行确实有大致路线。”阿婕赫对他说,“但换成你来走一定会中途改道,哪怕只是有你在场也会这样。”
“别说的好像我很特殊一样,本来就没多少人像你一样想往哪去就往哪去,毕竟也没多少人像你一样和谁都这么疏离。”塞萨尔抱怨说。
“但也没多少人像你一样不自觉地陷这么深。”听她的语气似乎微微笑了笑,意味深长,她似乎觉得这十分有趣。“刚抓住穆萨里的时候,你有很多机会出城,而且我相信,在这之前你也有很多机会。”她说。
“是有,但我的机会都是借助别人得到的,不
94
能就这么割舍。”
“里头没有可以让人轻易脱身的公平交易吗?”
“没有。几乎都是情谊,难道你和你兄长就没有情谊吗?”
她放慢了脚步,稍作思索。
“确实没有,”她说,“我和穆萨里的事情全都是公平交易,包括这次出征也是。”
“你们俩一定有个人有大问题。”塞萨尔说。
“当然啦。”她说,“有大问题的肯定是我,毕竟穆萨里在部族里是每个人都尊敬的领袖,我却是那个会搞糟事情的人。”
阿婕赫从最后一段残破的石路走上城墙,塞萨尔也随后跟了上去。他把视线在身后残破的狗坑停留了片刻,接着才眺望起城外军营海一样的大帐。这些帐篷从城墙几里外一直延伸到更远方的山脚,地上筑着很多土墙,插着很多木桩尖刺,地下也挖满壕沟工事,帐篷中央还有数不清的马匹和车辆,驼满了他们的军需物资。
从辎重队的规模来看,这些物资够他们撑到初春。也就是说,草原人其实不会围攻诺依恩围攻一整个季节,他们最终还是会在春季来临前回到大草原,畜群需要在夏天以前赶到夏天草场,春季播种也需要很多人手。
不过,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
塞萨尔扫视一圈,最终把视线落在更远方,那儿正是往北方去的大道。在道路尽头,可见奥利丹的军队正在缓缓接近,由于人均身披盛装,因此比起当时急行军过来的萨苏莱人,他们看着更像是节日里接受国王检阅的依仗队。训练有素的军团组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阵穿过雪地,大风吹过时,可以在晨曦中看到近百嵌有金边、红黑相间的雄狮旗在军阵上方飘扬。人站在城墙上眺望,很容易觉得自己是正在检阅军队的国王。
“真够浮夸的。”阿婕赫说。
“他们也不是来打仗的。”塞希雅从城墙那端的塔楼走了过来,“我们在北边打仗的时候不会有这种阵仗,要是有这种阵仗,就说明一场战争到了尾声,有大人物要来见证宣告战争结束的仪式了。”
“你们的俗话是怎么形容这种场面的?”塞萨尔忽然问了一句。他觉得气氛不太对,如果他不开口缓和气氛,多半会有他不希望的事情发生。
“干嘛问这个?”
“我只是好奇你们雇佣兵团体私下是怎么腹诽和抱怨他们的。”
她把嘴一撇。“有人来兴师动众逛窑子了。”
塞希雅边说边踱步过来,先盯着阿婕赫腰间的短剑看了一阵,然后专注地打量她这一身厚毡衣,似乎在估计她的体态和身形。过了一会儿,塞希雅终于开口了:“没错,当时突袭了塔楼的刺客就是你。你很轻易地结果了所有人?”
塞萨尔闻到一股微妙的剑拔弩张感。
“也不是所有人,要不然,怎么还会有风声传出去?”阿婕赫回说道。
“这么说是很轻易了。”塞希雅琢磨着说。
“你不参与那边的迎接仪式吗,老师?”塞萨尔迫不及待地插话说。
塞希雅微微一笑。“我从没出席过这么庄严文雅的场合,以前是轮不着,现在是不习惯。比起这个,我更好奇当时发生的事情。”
“我跟你一样各为雇主做事,如果杀了你的人,那也没什么可请求你原谅的。你该不会是来研究怎么切断我脖颈的吧?”阿婕赫反问道。
“这倒算不上,”塞希雅伸手拍在塞萨尔肩膀上,“黑剑为钱办事,干这一行,死在战场上自然没什么可说。不过塔楼里的人死的这么轻易,我还是很惊讶。现在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挺好奇,从事你们这一行的看待我们可怜的人类,是否和屠夫看牛羊差不多?”
“我不是屠夫,不懂他们怎么看待牛羊,不如你先告诉我屠夫会怎么看待牛羊吧。”阿婕赫把问题抛了回去。
“吃掉它们。”塞希雅敛去微笑。
“我可以担保这家伙不吃人。”塞萨尔立刻插话说,“吃人的那个现在......”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是否吃过人,塞萨尔。”阿婕赫开口说,“如果你想给别人展示无条件的信任,那我觉得这毫无意义;如果你是想避免冲突,那我觉得伤口越拖,反而越容易化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