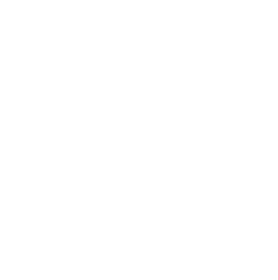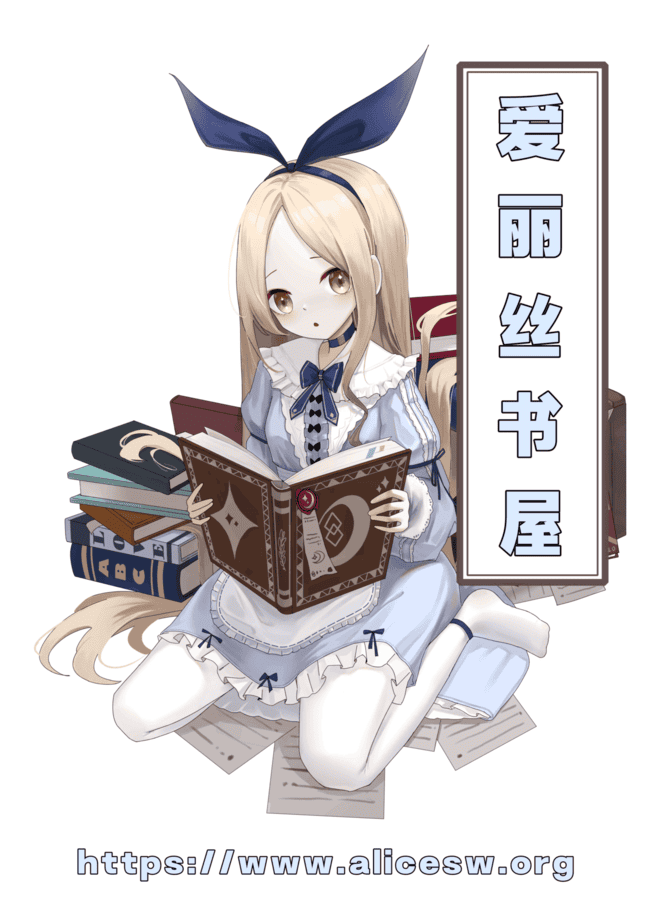......
再次深入智者之墓后,塞萨尔发现墓室的结构已经超出了他对墓室的认知。从一扇位于地板的窗户走出后,他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座凌空的楼梯上,楼梯则装在一面壮观到不可思议的巨墙上。往左或往右,怎么都看不到尽头,往下看是一片深渊,往上看则是一片不见穹顶的迷雾。
这地方似乎是个林地,不过,不非法兰人时代经受过大量砍伐的林地,更像索茵小屋旁边的巨木森林,甚至还要更古老,像是荒原那座栖息着真龙的森林。仿佛和世界一样古老的巨树看起来比现实世界最高的山峰还要高,往下深入无底深渊,往上深入穹顶的迷雾,树枝之宽阔仿佛古老的大道,茂密的树叶更是如不透光的华盖般层层遮蔽着视野。
凌空的楼梯从身后的窗户连接到一条树枝,随后消失不见。树枝尽头处可见树干上开了一小扇门,门后阴影中依稀可见一口木棺。棺材的木头是原木,看起来是巨树的一部分,墓室本身和墓室中的一切陈设也是在树干中挖掘和雕刻出的。另有一口木棺就架设在几十米远的另一条树枝,颇像是个鸟巢。
树坟?
他们沿着树枝之间架设的梯级往下走了很久,在一个不见光的分叉墓室前,阿娅警觉地后退一步,避开一个只看剪影就熟悉无比的暗影,塞弗拉大喝着让她自己现身。随着阿婕赫扑过去迅速挥出一剑,朦胧不清的暗影消失了,只有她脸上的一道伤痕和对方溅在树干上的血证明另有一个塞弗拉存在过。
塞弗拉摇摇头。“你太亢奋了。”她对阿婕赫说,“难得没有碰面就消失了,我还想问问自己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可是个我能光明正大杀死的塞弗拉。”阿婕赫耸耸肩,“多难得的机会,而且我还能当着你自己的面把你的头切下来做收藏。”
“现在看来,发生的意外大概率是和残忆有关。”塞萨尔让这两人打住说,“不同时间的混淆越来越严重了,不管其它时间发生了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握着彼此各自的手......”他说着看向阿婕赫和塞弗拉,“对,我说的就是你们俩,别两句话就动手行吗?就当是在墓地里各自退让一步,回到现实之后随便你们怎样。”
阿娅严肃地掩着嘴咳嗽了一声,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往下走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巨树的底,但他们到了另一个通往墙边窗口的梯级,打算就近落脚,出了麻烦就沿着窗口出去。这地方的树枝已经结成了巨大的华盖,看着就像个市民广场,树干中挖出的木头墓室有十多个,散乱分布在许多地方。虽然阿婕赫对在墓室里缠绵颇有兴致,但塞萨尔没什么劲头,最终他们还是在华盖上搭好了帐篷,准备在这地方过夜。
合拢帐篷布之后,外面是永燃的篝火,内里则是一片漆黑。塞萨尔躺在帐篷里,两条胳膊一左一右,左胳膊被阿婕赫枕在脖子下面,右胳膊枕在狗子抱在胸前。尽管姿势不同,但这两个非人之物的牙都咬在他身上,带着各自渴望舔了满嘴的血。
如果他还是祭台上最初那个人类,他现在一定已经失血过多致死了。
说到底,这两个家伙都是渴血的孽物,也就是靠着他一直用自己的血肉饲养才没放出去祸害他人。塞萨尔总是以不必要的道德感要求自己,所以每次看着这一幕,他都有种自己正在饲养恶魔等着残害人世的感觉。时至如今,他也没见得改变她们的习性,只是尽量盯着她们时时刻刻做要求而已。
阿婕赫侧身舔舐着他肩头的伤口,顺着他肩部往上,一直舔到他唇边。然后她舔了舔嘴角,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的脖子,将雪白的身体趴在他身上,贴在他胸前。塞萨尔抬起膝盖,感觉她两腿间的柔唇贴着他的大腿滑了过去。
他揉捏阿婕赫白生生的圆臀,抚过她臀后微微耸动的狼尾巴,感觉她大腿间的双唇像绽开的花瓣一样向外鼓了起来,贴着他的大腿微微蠕动,随着摩擦往两侧翻开,不住淌下湿滑的液体。
塞萨尔咬住阿婕赫的嘴唇,和她轻轻地接吻。他感觉狗子抱住了他的胳膊,脸颊也埋在他发间,带着温热的呼吸咬他的耳垂。狗子把他的耳朵含在口中舔舐,发出湿漉漉的唾液搅弄声和滚烫的呼吸声。
狗子的右胸和阿婕赫的左胸压迫着他的胸膛,挤在一起,两枚珠子也在他皮肤上紧紧贴着,好像两枚小巧的舌头在交缠挑弄。他那条蛇在她们俩紧贴着摩擦的白皙肚腹间滑动,一会儿贴着阿婕赫小腹的纹理抵在她肚脐上,一会儿贴着狗子的下腹的纹理滑入她身下的双唇,感到了一股迷乱的快慰。
他抓住两个人的臀部揉捏,不时拍打,狗子口腔的炙热感越发强烈,他的左耳朵几乎是要融化在她的唾液中,失陷唇瓣的吮吸和香舌的舔舐里了。那条从中线分开的长舌头把它缠了一圈又一圈,好像捕猎的蛇。阿婕赫的脸颊也逐渐泛起了浅红色的醉意,她仰起头,用双腿夹住他的手,发出一声喘息,然后又低下头,咬起了他的脖子。
塞萨尔感觉狗子的手落在了蛇头上,阿婕赫的手抓在了蛇身上,一个绕着蛇头挑弄,一个抓着蛇身摩挲。他抱着阿婕赫的细腰,把手指伸到狗子嘴唇中,由她吮吸和舔舐,然后抓出她香软的舌头揉捏。他感觉自己的身子很慵懒,灵魂也充满倦怠,精神上甚至有种迷失在这里也不为过的臆想。
不知怎么的,他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情形,看到迁徙的鸟群掠过天空,看到手掌大的精类在林地中穿行,看到他的主人抓着一条毒蛇对她姐姐炫耀,说这东西的花纹比城堡的雕纹还要漂亮。他的童年时代就是跟着他的主人到处走,看着她跟着她的姐姐到处走,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跟着他主人的姐姐到处走。
塞萨尔和菲瑞尔丝挤在她的床边,为她大声朗读她要求的法术理论,不时停下听她的纠正,说这个地方念得不对,具体哪里不对,菲瑞尔丝又说不上来。等到她咕哝着睡下之后,塞萨尔给她盖好被褥,却看到亚尔兰蒂像个幽灵似的飘了进来,一头白发,肌肤好似冰雪。
“世界像个没人再上发条的机械钟一样走向终点。”她意味深长地说,“非造之神已经失去一切,只余空洞的躯壳,谁会重新让它回归昨日?谁会让它再次拥有智慧?”
“没人去上发条,机械钟当然会......”
“还没到机械钟出现的年代。”亚尔兰蒂说着来到他身边,把手按在他额头上,那只手五指纤长,寒凉如冰雪。“你来自何方?”
“我不知道。”塞萨尔摇头说,他感到一丝畏惧,“我只是下意识回答。就像先知的预言一样,有时候会有破碎的词句和印象在我的记忆里出现。您不是也在说着这个时代没有出现的东西吗?我们明明都是十多岁的......”
“我确实是个十多岁的少女,但我不完全是,就像你也不完全是一样。”她说着来到菲瑞尔丝身边,“你知道吗?我既是她的姐姐,也是她的母亲,甚至是她的祖母,是她祖母的祖母,是......”
“你们的母亲还活着。”塞萨尔说。
“不,”亚尔兰蒂笑着来到他身边,“还活着的只是一个忘记了如何去爱的老女人罢了。生下我们姐妹俩这件事,可不是由她来做的。”
“您让我有些惶恐,大人。”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在学派里听到主人的秘密是我们这些人的寻死之道。”塞萨尔说。
她飘到他身后,弯下腰,握住他的肩膀。“那你害怕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吗,亲爱的?”
“您可以让我做任何事,而不必这样威胁......”塞萨尔摇头说,接着他发现她握住他的手,放在她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胸口上,顿时脸涨得通红。
她笑了,“从我们把你从多头蛇里剖出来那天起,我就没见你脸红过。人们都对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女仆毫无戒心,我却发现了你的不同。现在你的脸红的像樱桃一样,是否说明我的猜测有我的道理?你认为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有,你如果再陪我的妹妹过上几年,是菲瑞尔丝会爱上你,还是你会爱上菲瑞尔丝,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只是担心,”塞萨尔说,“明天您还要上早课,如果您的导师发现您精神疲倦,也许会追问到我头上。”
“就算我找个人缠绵一整个中午,带着满脸红潮过去谈论学术,我的导师也不会追问我任何事。”
“那是因为等到米拉瓦来接您的那天,所有和您发生过关系的情人都会被处死,头颅献给皇帝过目。你们法兰贵族的习俗......”
“这么说,你认为我来找你,是想找一个将死之人排遣渴念?”
“你的导师会说,他要和一个在中午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性行为的年轻人谈论学术,而且他会把这件事写进——”
“写进密文手稿,”亚尔兰蒂飘到他身侧,把脸靠近过来,她的眼睛里蕴含着古老的恐怖,“你看起来沉默寡言,实际上你什么都知道。你就像个诡异的植物一样扎下了根系,记录和探知你看到的一切。我说的对吗?”
“至少我对您一无所知。”他低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