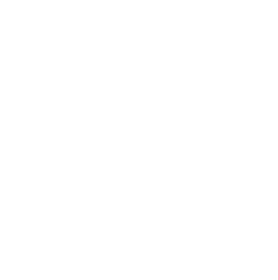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吗,主人?”狗子从他头顶弯腰俯视他,“你左手断面的血管就是证据。你已经进入这个受诅的国度了,转变是没法停止的。要么就放任不管,一直往下跌落,要么就抓住道途给你的绳索往上攀登。”
“这世界上就没有让人往后退一步的法子吗?”
狗子摇摇头,露出欢欣的笑容,就像她一直知道答案,只差在这告诉他了一样。
“有,”她带着微笑说,“用毒素抑制你的生机,让你皮囊下的血肉灵魂一点点腐烂,你就不会再跌落了,因为那样你就差不多是具还在走动的腐尸了。腐尸怎么会跌落或者往上攀登呢?”
他感觉自己的脸变阴暗了。“有人这么做过吗?”
“那些受诅之后还坚持自己人类身份的人都会这么做,人们把他们叫圣人,称其为伟大的坚持。你想当圣人吗,主人?”狗子带着怪异的好奇问道。
“你要是想,就得弃绝所有能满足你欲望的东西。”菲尔丝盯着他说,“你弃绝了自己的感官欲望,不会再感到欢愉,那你就不会再被诱惑,也不会再发生转变,就像荆棘缠满全身之后你就没法再碰到爱人的身体一样。”
“令人绝望。”塞萨尔说。
“我们最好快些。”菲尔丝咕哝道,“你还有事要做,而且再往前走几步也能帮你更好对付今后的危险。”
“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你。”
“你会感觉到我在引导你的心灵,只管听我的话就好。”菲尔丝朝
45
前倾身,抓住他一条胳膊,抱在她酥软的胸脯之间。
尚未等塞萨尔体会其中微妙的感受,菲尔丝就张开了嘴,他以为她要咬住,谁知她把他左手断面一口含了进去,轻轻一吮,就带来一阵强烈的酥麻感,汩汩血液涌入她喉中。过了一会儿,他竟然看到血液散发出的红光透过她喉部皮肤传了出来,好似那儿只有一层半透明的薄膜。
他的头脑忽然间变恍惚了,今夜本来寒风凌冽,他却发现屋内的风完全停息了,仿佛是空气凝固了,令人觉得气闷。
塞萨尔盯着在她皮肤上蔓延的分叉红光,感觉她咽下的血和他产生了某种联系。因为这联系,他能嗅到她血与骨的馥郁芳香,令他体内某种非人的感官渴望蠢蠢欲动。
“我在带你接触世界的另一个面目,所以不要挣扎,不要从我怀里挣脱......”
菲尔丝话音分明很轻柔,他却觉得,从她口中蹦出的每个音节都如同尖针划过陶器,莫名显得尖厉刺耳。不止是她的话音,许多声音都变刺耳了,哪怕她呵气的声响都要刺得他耳朵滴出血来。各种细微的环境音本来很难察觉,这时都转为尖厉的嗞嗞声,将他淹没,如同铅一样沉的汪洋包围了一尾鱼。
她的形体蓦然间消融了,他看不见她在哪,只能感觉她趴在他背后。这一刻,他感觉她两条胳膊环在他脖子上,下一刻,他感觉她的呼吸吹在他肩上。周遭世界的稳定轮廓蓦然间解体,床、柜子、桌椅、墙壁都像火炬下的人影那样向外延展,远端隐入黑暗的帷幕中,远超出他的视野之外,近端如利爪抓在他身上,想要撕裂他的皮肤。
整个房间都变得如同密林深处,遍布着深红尖锐的枝杈,遮蔽了每个方向的视野,连天空都无法看到。
在这深红色密林中,许多颀长的节肢屈张伸展,许多臃肿的触须抽搐摆动,许多沾满血的大嘴撕裂开来;许多怪异的眼珠在血色枝杈上骨碌乱转,许多狰狞的血骨堆积成山,许多流着血的空洞面孔在树木缝隙中爬动,好像扁平的尸蟞。
“这附近接触外域的只有城堡里那几个老家伙,但他们去的地方不是猩红之境,所以我们不会遇见其他同路人......不,那儿有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个头很高,被锁在.......没事了,她被锁链束缚着,没法接近我们。总之不要从我怀里挣脱......”
菲尔丝还在说话的时候,什么东西忽然扑了过来,凝滞的空气中卷起血雾。一只血红色兽爪抓紧前方的红木树干,颤巍巍的兽毛泛起涟漪,像是位于水下一般无风自动。塞萨尔看到枯瘦的肌肉依靠清晰可辨的肌腱维系在枯瘦的骨骼上,协同一致地使力抓握,压碎了树干上乱转的眼珠。
这只兽爪正在缓缓靠近他,似乎想要触碰他,但它悬停在了他几步之外,像是被什么束缚住了一样无法前进分毫。
一个听着很遥远的声音从交错的深红色枝杈后传来。“你从哪儿来?”
菲尔丝立刻在他耳边低语起来,“跟她说我们是意外接触了祭祀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完补充了一句,“我是走我们学派的办法附在你身上偷摸进来的,她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说话。”
说话的人似乎很期待回应,于是塞萨尔传达了菲尔丝交待的答复。
“你为什么被锁在这里?”他说完也补充了一句。
“我不是被锁在这儿。”树木背后的那人说,“我是被困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就像被拴在一根钉死的木桩上,哪怕把灵魂投射过来也没法走出太远。”
“你住在城内吗?”塞萨尔问道。
“我在城外的军营里看着你们呢。”对方话里带着戏谑。
“你是萨苏莱人?”塞萨尔心有所感。
“一部分算不上。”她答道。
塞萨尔转而想到了卡莲修士的故事,问道:“那你是野兽人?”
“一部分算得上。”她并无诚意地给了个同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萨苏莱人允许自己的部落子民探询异神阿纳力克?”塞萨尔锲而不舍地问道。
“没有这个说法,”从那边飘来的声音很悦耳,每个字似乎都带着催人遇睡的感觉,“只是我们这个种群生来就和世界的另一个面目相连,受人憎恨、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披上厚毡衣,把自己裹在密不透风的兽皮里。”
野兽人与生俱来就和所谓的外域——或者说世界的另一个面目——相连?这话听着实在匪夷所思。塞萨尔更愿意相信是野兽人种群里有一些稀少的个体生来如此,这样的话,卡萨尔帝国若想把野兽人当军事奴隶用,只要单独找到那些特殊个体提前扼杀就好。
“小心她的话音!”菲尔丝咬着他耳朵说,“这个道途上走得远的人会引诱后来者把他们吞下去。你们本来就是跟无止境的渴望相伴的。”
46
确实,她说起话来就像念诗,用温柔异常的声调掩饰她那只尖锐枯槁的兽爪,好像扮成外婆的狼在引诱小红帽接近自己似的。塞萨尔觉得这个意外相遇很有意思,这事告诉他,萨苏莱人的军营里也有一个掩饰身份的孽怪,并且,随军法师的失踪可能和她密切相关。
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她似乎有意在话中揭示自己的身份特征。这事很怪,有可能她是在散布假消息,诱使他对一个无辜者动手,但也有可能,她是诱使他杀害那个困住她的人。
这样一来,她就能得到解放?从某个困住她的囚笼中?
“总之,”对方说,“我在猩红之境待了很久,既然你才把灵魂投射过来没多久,也许我可以给后来者一些引导和建议。我想,身为一个探询外域的人,你也不会关注俗世间的争端吧,你觉得呢?”
他觉得什么?他可能是诺依恩最关注这场世俗争端的人了,整个诺依恩也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关注。
“一部分算得上。”塞萨尔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谎话,末了还补充了一句,“但我会关心我跑不跑得掉。”
“别担心,但凡你在这片林地多走几步,四处探索探索,你就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了。或者你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探索?”
菲尔丝又咕哝起来:“别听她的!呃,好吧,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你可以稍微听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她有没有在骗你。”
“一直以来,我都是跟着一本古老的经卷做祭祀。”塞萨尔想了想说,“很多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我可以听出你给的建议是真是假。”
“那就让我的建议更具体一些吧。我需要仔细观察观察你,然后才能告诉你什么法子最适合你。”
声音停下来,似乎在等待他的回应。塞萨尔没法子,只能点头答应。
“把头抬起来,伸长你的脖子。”她说道。
塞萨尔闻言做了这个动作,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猪仔在给一头狼展示自己的肉质。
“很好,”对方攥着树干,轻轻舒张利爪,划过那些血淋淋的眼珠,“这脖子的线条纹理不错,颈项中心的凸起正是最叫人钟爱的那种。你和我不同的地方在于皮肤太白,不过等涂满了血,也就没什么区别了。顺着这个诱人的人类脖颈往下——你看起来不太接受这个形容词?”
塞萨尔承认他还是头一次被人品评,这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乍一听,她是在赞叹他的身体轮廓,但仔细一想,对方这个赞叹其实就像他赞叹卤好的鸭脖子,所谓的涂满了血,用他的话说就是涂蘸料。
“我们不妨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塞萨尔道,“在你表达吞食欲望的时候,我是在椅子上,还是在餐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