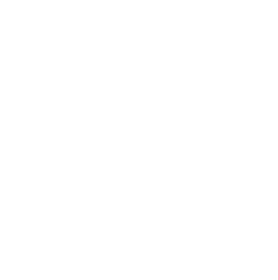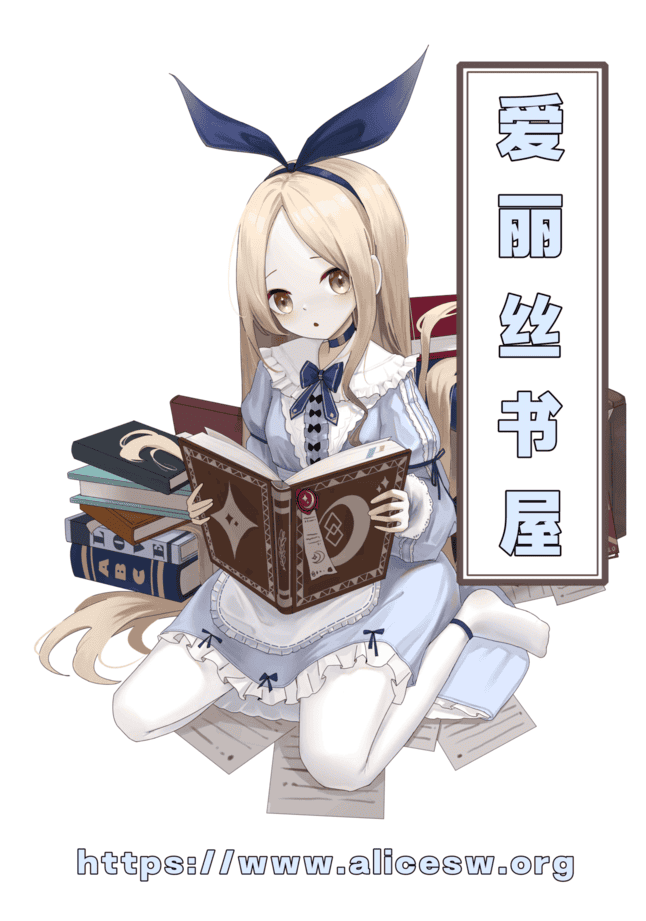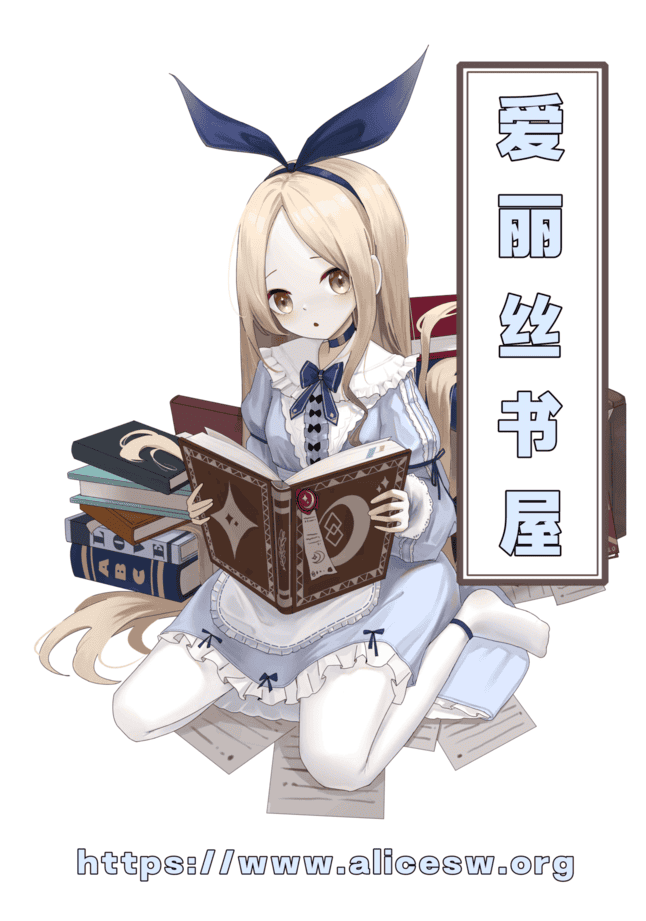刘牧之抱着妻子的尸体。
脸上不见哀戚,只被莫名的茫然所充斥。
直到孙儿开始哭泣。
悲伤才迟迟传递过来,他一下湿润了眼眶,轻轻呼唤着妻子的闺名。
熟悉的温柔回应忽自怀中响起。
“郎君。”
他惊喜低头。
“娘子,你没……”
一对嵌在死灰面孔上的充血眼球直勾勾对着他,血液渗出眼角流淌染得嘴唇鲜红。
温柔声音骤然尖利。
“为何要害死我?!”
毛发顿时倒竖。
刘牧之猛地推开尸体,护住孙儿,一把抓起腰间金瓜。
正高举,再看去。
妻子双目紧闭,面容端庄如故,哪儿有血泪流淌?
幻觉?
“父亲?父亲!”
屋外传来呼喊,却是一向循规蹈矩的儿子披头散发怀抱着个圆滚滚的事物跌跌撞撞冲进来。
刘牧之习惯性地要呵斥,可一扭头——儿子衣衫满是血污,而那圆形事物分明是一颗人头,仔细看,是自己的儿媳。
“你……你做了什么?”
儿子举起人头,仿佛在夸耀什么功绩。
“父亲又糊涂啦?咱们要予法王请罪,自得备上大礼。”
说着,瞧见母亲的尸体,更是大喜过望。
“母亲死啦?倒也省事。”
便把人头系在腰间,掏出把短刀,兴冲冲过来。
“逆子!”刘牧之惊骇莫名,“住手!”
儿子果然罢手,却道:“是啦,为人子女怎可毁坏父母遗容?”
目光一转,落在孩子身上。
“哎?这小畜生细皮嫩肉拿去送礼岂非更佳?”
说罢一把揪住孩子总角,眉开眼笑着竟是要当场割取亲生孩子的头颅。
刘牧之大惊,情急之下,拿金瓜砸倒儿子,抢过孙儿撞门而出。
留得身后。
“父亲。”
儿子抱着人头瘫坐在地叫唤着。
“你要害死我们吗?”
刘牧之浑身冰寒,奔逃愈发狼狈。
慌张跑出后院。
“来人,来人……”
呼呵几声,愕然见着廊中积血成泊,随他转战多年的亲兵竟在互相砍杀,兵刃卡在骨头拔不出,便野狗般用牙齿来撕咬。
惶惶路过庖厨。
烟气自半开房门里滚滚而出。
大锅腾腾冒着白气,烟笼雾罩里,伙夫、婢女们把自个儿用铁钩吊在房梁上,同腊肉熏鸡挂在一处,一扇一扇齐整排列。
惊骇逃至中庭。
供奉多年的老法师宛若疯魔,四处抓人,凡被他攥住,便用铁锥刺烂双眼,挑破耳膜。
刘牧之不敢停留,抱紧孙儿,小心绕开。
可他很快发现,府中各处不是在自相残杀便是以各种方式自戮,惨叫避无可避,哀嚎躲无可躲。
疯了?都疯了么?看,天亮了,天已经亮了,已经是白天了!
刘牧之语无伦次地嘶喊着,可无人理会他,他的子女、他的妻妾、他的部下、他的奴婢……身边的一切人等,除了他与怀中的孙儿,统统陷入了凄惨的癫狂中无法自拔。
直至。
“东主。”
他猛回头,老供奉紧闭着双眼出现在面前。
不等他下意识挥出金瓜,耳边:“听我说!”
“护宅法坛已为恶鬼所破,老朽撑不了多久。”
“可规矩……”
“狗屁规矩!”
老供奉喉头像含着血,字字含混又滑快。
“眼下动手的应是‘替生’、‘换死’两头大鬼,‘替生’有目即可乱人心智,‘换死’有耳即可惑人魂魄。欲保存性命,当……”
最后一句,老法师几度张口,也是无声。
刘牧之急切追问:“当如何?”
老法师忽的上前,将滴血的铁锥塞给刘牧之,翻开眼皮,但见其两个眼洞中皆是血肉模糊。
眼球已被捣成烂肉。
刘牧之饶是沙场宿将,冷不丁也被眼前吓得连退两步。
老供奉没紧随上前,他用手指抵进耳朵,用力一捅。
同时张口呼喊,虽不闻声,却分明是:
“逃!”
刘牧之楞了稍许,转身埋头狂奔。
他逃至前院,百十步外见着一面影壁,影壁便是大门。
可这时,被他抛到身后的哀嚎与惨叫却追了上来,如有实质,扯住他的衣袖,绊住他的脚步,于是这短短百十步好似被无限拉长,怎么也跑不完。
那些哀嚎,那些悲鸣,也伴着钟声越来越清晰,汇成句句质问。
“刘牧之!你要抛下我们吗?”
“刘牧之,为何要害死我们?!”
“刘牧之,你可知罪!”
字字句句叫他脚步愈发沉重,喘息愈发急促,终于,他狠咬舌尖,铁锈味儿溢满口腔换得些许清醒。
他拼命一挣。
跑不尽的百十步竟骤然缩短,那面影壁突兀撞到眼前。
意外的。
浑石雕成的影壁此刻却如沙筑土堆,一撞便碎,露出其后早已洞开的大门。
可门外却非熟悉的街景,唯见着重重楼阙盘山而起,巍峨入云。
刘牧之此生从未见过这般宫厥,哪怕梦里,可此时,他却喃喃着一口道出了其名字:
窟窿城。
耳畔的钟声还在响起,一声漫长过一声,仿佛永无尽时。
身后的哀嚎与质问再度追了上来,纠缠不去。
“刘牧之。”
他神情一怔,木木低头。
被一直护在怀中的孩子笑着问他。
“你可知罪。”
他惊慌抓起铁锥,在孩子眼耳边游移颤抖一阵,终究哭叫一声,丢开了铁锥。
无力跪倒下去,重重磕头。
“知罪。”
“知罪!”
“刘牧之知罪!”
碎石划开额头,鲜血和泪淋漓。
“只求法王慈悲饶我孙儿一命。”
…………
当钟声响尽。
人们看到的是磕烂了脑袋、跪死在大门里的刘牧之。
消息传得很快。
门前聚起愈来愈多的人。但没有喧嚣,只是抑声低语,或干脆噤声,更没人敢踏入大门一步,本该喧闹的白日,沉寂仿佛深夜。
依着惯例。
凡有横死家中,总会有僧道前来超度亡人,会有差役入场收敛尸身。
可今日却一概皆无。
这可是郡公,是左仆射,是节度使。
纵然已兵败失势,却仍是钱唐官面上有数的高官显贵。
竟由着他曝尸于人群的围观么?
“高官如何?”
“显贵如何?”
“声名再盛,胜得过法王之威?权势再大,强得过鬼神之力?”
几个无赖汉守在刘府边上,领头一个大声嚷嚷着,在一片低语中分外刺耳。
“凡夫俗子,住了大宅,穿了紫衣,使唤得几个奴仆,自以为成了人上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触犯鬼神威严,落得这般下场,岂不活该?岂不可笑?”
人群里不少各方派来的耳目,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听着这以下犯上的粗鄙话语,一阵哄闹,但终究无人敢冒头反驳。
人群不起眼的边沿。
闻讯而来的李长安作脚夫打扮,拿汗巾缠住小半张面孔。
“他既自暴身份,我以为已做足了准备?”
同样得信赶到的无尘,同样改换了面目,此时腰佩长剑,头戴斗笠,仿佛江湖豪客。他神情凝重,小声应道。
“刘施主确已有所防备,可哪知恶鬼竟坏了规矩,胆敢白日杀人!”
“规矩?十三家怎么说?”
“祖师们各有考量。”
“所以连收尸的也无一个?”李长安摇头,“前脚露了脸,后脚就灭了门。你的谋划怕要落空。”
“不然。”无尘立时言道,“做了解冤仇,岂有退路?他们都是聪明人,会想明白的。”
“想得再明白又如何?有刘牧之前车之鉴,谁再肯相托腹心?军合力不齐,如何与恶鬼相争?”
无尘张了张口,反驳在喉间几度回转,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只好再作计议。”
人多眼杂不是谈事的地界,两人正要退去。
刘府前,那无赖汉还在喋喋不休。
“这刘牧之好端端的富贵老爷不做,学人做什么‘解冤仇’。不错,就是那些阴沟里的老鼠,藏头漏尾的贼匪,沆瀣一气,四处作乱,自以为得势,结果呢?”
无赖汉啐了口唾沫,招呼同伴拿来碗饮子,补充口水。
“别看他死得凄惨,却也是法王慈悲。告诫某些人,什么事做得,什么事做不得,免得一朝连累家小、亲朋,成了孤魂野鬼,夜夜哀哭,向你讨命。”
仿佛应和话语,大街上竟真的听着低低的哭泣与惨呼。
细细听,分明来自大宅深处。
人群顿时哗然。
平旦才死,尸体或许还尚温,青天白日的就要作祟了么?!
“莫慌,莫怕。”
无赖汉却得意笑道。
“法王慈悲,只叫刘家人死了一半,里头呀不是死人在哭,不过是活人在叫。”
说罢。
刘牧之身旁那具小小的“尸体”颤了颤,接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蹒跚两步,却又跌倒在碎石里,探出小手茫然摸索,稚嫩的声音哭喊着:
“阿翁,阿婆……”
人群里颇有不忍,可谁也没上前,反而愈发屏息禁语,好似生怕吭出点声气,便会叫那孩子误以为是回应,纠缠过来,惹得鬼神误会。
其实大可不必。
那孩子的眼耳边渗出条条血痕,显然,耳已聋,眼已瞎。
李长安顿住了脚步。
“道长,莫要冲动,这是陷阱!”无尘急道,“潮义信在周遭布下许多好手,地下还定有大鬼埋伏,就等人自投罗网。”
“我晓得。”
李长安点了点头。
“和尚你说得对,做了解冤仇,岂有退路?”
又扯下汗巾,露出面容。
“刘牧之说得也没错,欲登高一呼,又怎可藏头露尾?”
“等等。”
无尘神色变幻一阵,重重吁出一口长气。
“我来!”
“我是十三家门下亲信,恶鬼也不敢对我如何。解冤仇这杆大旗,就该我来挑。”
“正因如此。”李长安笑道,“唯独你不可。”
说罢。
越众而出。
步向刘府。
人群骚动退后,顷刻空缺下一块。
无赖汉没作阻拦,当头那个啐了一口,恶声道:“本以为爷爷今日是白费口水,没成想,竟真有个带种的!兀那汉子,姓甚名谁?”
李长安回答他,或说回答窟窿城,回答十三家,回答钱唐城内外几十万活人与死人。
“我乃上景门道人李玄霄。”
不再理会他,径直跨过大门,轻轻扶起孩子。
“阿翁?阿婆?”
孩子怯怯唤了两声,渐渐抿紧了嘴,不再出声,只紧紧抱住了李长安的手,止不住的轻轻抽泣。
李长安半跪着为他掸去些灰尘。
起身回望。
门外是乌压压的人头,各色的人等带着各色的面孔藏着各色的心思。
道士平静道:
“我亦是解冤仇。”
…………
两人兵分两路,无尘暗里去寻求援助,李长安则留下搜救幸存。
循着呻吟,他从尸体堆里翻出几位重伤垂死的武士。
沿着哭嚎,又打柴房、畜栏中制服了几个发狂的仆役。
顺着啜泣,自一口老井下找到一个惊恐的婢女。
她和同伴被幻术所欺,争相投井。当钟声响尽,恶鬼离去,她清醒后的第一眼,只见同伴的尸体堆叠着将自己托出水面。
她吓坏了,几乎丧失了言语能力,只剩下哭泣,但难得神志还算“正常”。道士便把刘家遗孤交托给她,自己腾出手继续搜救。
诚如无赖汉所言,恶鬼留下了小半活口,约么五十来人。然而,他们不是肢体残缺,便是已精神失常。可以预见,倘若没有李长安,残存者只会被困在刘府,在痛苦与癫狂中哀嚎至死。
这就是鬼王的“慈悲”。
…………
府内一间较为偏僻狭小的院子。
院墙上绘有符图,角落放置有镇物,中间是一座小庙,庙里供奉的除了刘家的先人,还有二十八具铠甲,历经战阵但养护得宜,顶上各悬有黄布星图,正合斗宿,或许是某种法术的载体,可惜内里泥塑已裂,甲胄神光已晦。
种种布置表明这间小院大抵是刘家准备的避难所,不知为何,没起到什么作用。
道士便把幸存者安置在此,庙中神台也清理出来放置伤员。
完了,正准备弄些食水疮药。
可一扭头,幸存者里竟相继出现低烧、抽搐、呕吐乃至伤口脓肿的症状。早上才受的新伤,半天不到,怎么可能化脓?甚至,李长安自己都感觉到微微的不适。
“是鬼瘟。”说话的是名老者,“鬼王手下有一痈疟使者,它在府中播下了邪疫,但凡踏入刘府,必染瘟病。”
这老者是道士自一处庭院中找到的,那庭院里有十数人,人人眼睛被刺瞎、耳膜被戳破,老者亦是如此。当时,道士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只以为是个刘家老仆。
但而今看来……
“老丈是?”
老者撩开白发,流淌脓血的左耳后,以血为墨,画着一只假耳。
“老朽是刘家的供奉,也是这间庙子的住持。”
老者自言是刘氏老臣,在刘牧之尚且得意时,便在其军中为他安抚战殁亡魂,贬斥钱唐后,府中防治恶鬼的种种措施也由他操持。
今晨,不料恶鬼坏了规矩,白日作祟,他措不及防,被破了法坛,遭到反噬乱了神魂,动不得法力,无奈下,只好自毁耳目来摆脱幻术,又混在仆役、卫士中以求保存性命。好在晨钟鸣响不长,恶鬼又忙于抄掠财物及剥取死人魂魄,倒叫他逃过甄别,侥幸活命。
“院里布置犹在,老朽再调息一阵,稳固了神魂,启动禁制,或可稍稍抑制邪疫蔓延。”
“只是……”
“只是什么?”
“鬼瘟不止会感染活人,亦会沾染于食水、器物、风息之间。”
老供奉眼角脓血滴落。
“刘府已是死地。”
…………
“大师,我家师傅去城北娄善人家祈福去了……啊?娄善人上月就死啦?那、那便是到山上堪舆去了。”
斋房外,小道童语焉不详。
“无尘师兄且回,主持交代了,本寺暂闭山门,不理坊间俗务。”
山门前,迎客僧神情闪躲。
“刘家的娃娃是口挂起来的铡刀,我犯了失心疯把脑袋递过去?怎的,刘家贵种的命是命?我们兄弟的命就不是命啦?”
暗巷中,汉子振振有词。
…………
刘府里再碰头。
两人彼此都没想到情况会如此严峻。
大门之内,瘟疫肆虐,活人奄奄一息。
大门之外,恶鬼并其爪牙的凶恶目光一刻不离,没人敢伸出援手,甚至街头小贩都被远远驱离,不敢卖进来一碗水一口粮。
刘府好似被抛弃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更糟糕的是,舟船上能正常活动的只余两个半,一个道士、一个和尚、半个老供奉。
老供奉神情惨然:
“刘牧之,刘牧之!早说你运势已颓,安心作一富家翁,苟全性命又何不好?偏偏不甘心,偏偏不信命,偏偏去做什么解冤仇!落个人厌神弃,眼看要断子绝孙!真是蠢货!”
“老供奉何出此言?”
无尘道。
“仆射为公义而死,钱唐人嘴上不说但定记在心里,豪杰之士又岂会坐视其血脉断绝?”
“是么?”老供奉冷冷道,“他们在哪儿?”
无尘正色道:“他们只是一时被恶鬼伎俩所惑,只消咱们熬过今夜,他们定会醒悟,也定会群起响应!”
“熬?谈何容易。”
“仆射为苍生而死,贫僧又岂会惜命?”
无尘唱着“阿弥陀佛”,但此时倒更像个江湖豪客。
“有贫僧,有李道长,有老供奉您,等闲几头大鬼来犯,又何足畏之?”
老供奉神情缓和了些,但依旧惨淡。
“老朽晓得大师佛法精深,也听闻过李道长的本领,可窟窿城中的鬼使岂止几头?更何况,还有那……”
虽然嘴上说是恶鬼狡诈才让自己猝不及防,但侵晨时的恶鬼来袭的寒气分明还缠在骨髓不去。
当时情景仍旧一帧一帧深刻心里。
巨大的骷髅在浓雾中探出屋脊,被它驱使的怪物混着雾气攀过墙垣,涌入府邸,几乎一瞬间,就摧毁了他布下的禁制。神祠里每具铠甲里都温养着一位战死沙场的猛将,以秘法供奉多年,勇猛更甚生前,可仅仅几个呼吸,便被那些怪物分食殆尽。
他声音艰涩吐出怪物的名字。
“魙。”
小院里冷了一瞬。
疯子的哭嚎与伤患的呻吟愈加刺耳。
这个字眼仿佛自带一种冰冷、一种魔力。
“无妨。”
李长安的话语从容响起,驱散寒气。
“鬼王在钱唐横征暴敛,不惜惹得上下怨愤,不就是为了立它的庙宇么?要立庙,鬼使是它的脸面,魙是它的底气。李某一介野道人,无尘大师它奈何不得,刘家也只余残孤,它肯在咱们身上折损脸面、毁坏底气么?”
“这……”老供奉愕然,“这不是在赌么?”
他还以为李长安敢当出头鸟是胸有成竹,难道还真只出于一腔血勇?
“事到临头须放胆。”李长安却笑道,“退无可退,何妨一搏?”
这显然无法说服老供奉。
他其实同那老井中的婢女一样,也被吓坏了。
慌乱惨淡间,竟说出要集体自戮,恳求无尘将他们的魂魄带出刘府,以免坠入窟窿城的话来。
无尘只好搬出十三家,劝慰他,已经传信各位祖师,为刘家求取庇护,稍等些时候,当有回音。
然而,若十三家有意插手刘家灭门一事,早上也不会任由刘牧之暴尸于众目睽睽之下。
老供奉也清楚,但有希望总胜过没有。
他忧心忡忡又怀着某种决绝去布置今晚应对恶鬼的防务。
无尘懂些医术,去看顾伤患。
至于李长安。
……
“老爷,不好啦!”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院里翻墙进来一个短毛汉,张口就讨要米面酒肉。”
“好个狂贼,乱棍打出去。”
“可……可他是从隔壁刘家翻过来的。”
“啊?”
“他说自己是解冤仇。”
“啊!”
“他还说,若腹中饥饿身上没力,夜里斗不过厉鬼要逃跑,就从咱们这儿借过。”
“亲娘咧!快快,他要啥给啥。”
……
李长安赚来了好些酒肉,还有急缺的药物。
又一“好消息”紧随而来。
无尘的依仗,老供奉的救命稻草——十三家的使者姗姗来迟。
“什么?!”
无尘又急又怒。
“刘家平日供奉神佛殷勤,而今横遭大难,唯剩一遗孤被恶鬼欺凌,我等怎可弃之而去?!”
“师兄莫恼。”使者劝道,“这是栖霞楼的命令。”
无尘骤然沉默。
十三家的祖师不喜人间污浊,平日大多在城外栖霞山别苑修行,而栖霞楼立在栖霞山最高处,向东可望海上波涛壮阔,向西可观钱唐万家灯火。
栖霞楼便成了十三家祖师们参禅论道的地方。
也就是说。
召回无尘,是十三家一致的决议。
……
刘府门前。
人群早已散尽。
街市上空空荡荡,家家门窗紧闭,仿佛这不是汇聚天下繁华的钱唐,而是十室九空的中原某个荒废的城市。
残阳斜照,更添萧瑟。
“言尤在耳,小僧却要背信而去。”
无尘迟疑再三。
“若事有不谐,道长可……”
李长安打断他:“我省得。”
无尘叹息一声,望着道士,眉头忽的又皱了几分。
“道长没带兵刃?”
“刘氏乃将门,不缺兵器。”
“凡铁怎可斩恶鬼?”无尘摇了摇头,解下腰间配剑,递将过来。
李长安接过,拔剑一观。
神光湛湛,秋水照人。
“好剑,无功不受禄。”
“非也。”无尘道,“好剑正配好汉,若束之高阁与朽木何异常?道长千万收下,权且照顾小僧愧意。”
道士也就不再推辞。
想了想。
从身上取下一葫芦还赠无尘。
这葫芦是黄尾死皮赖脸从万年公处讨来的,因解冤仇之事闹大,黄尾又交托给了常常进城的李长安。里头装着能稳固魂魄的槐酒,葫芦本身也能随着魂体变化,算是件宝贝。
无尘同样不推辞。
打开葫芦一嗅。
“好酒!”
他郑重道。
“待明日与道长共饮。”
……
无尘在使者的催促中离去。
道士抱着宝剑。
倚在门边。
静待残阳落尽。